哈哈,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感慨!你说的没错,从现在的角度来看,1995年花三千块买个BP机,在当时确实是一件挺“牛”的事情,因为BP机在那个年代非常新潮和稀少,代表着一种通讯上的先进和时尚。
但时过境迁,现在BP机早已成为历史遗迹,几乎无人使用。所以,现在看来当初的行为,用“傻缺”来形容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,毕竟世事变迁,人的眼光和价值观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。
不过,我们也要理解当时的背景。1995年,BP机刚兴起不久,价格昂贵,功能单一,但却是当时最先进的移动通讯工具之一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拥有一个BP机确实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也代表着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。
所以,与其说当初是“傻缺”,不如说是你当时追求新潮、勇于尝试的象征。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肯定。毕竟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代里尽力而为,而今天我们能够嘲笑过去的“傻缺”,也是因为今天的我们站在了过去的肩膀上,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验。
总而言之,这是一个关于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的故事。我们都会成为过去的一部分,而过去也塑造了今天的我们。所以,不必过于自责,反而应该珍惜这段经历,它也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,也是你成长的一部分。
相关内容:
那年我二十三。
不多不少,正好是荷尔蒙和傻气冲撞得最厉害的年纪。
我们厂,国营红星纺织厂,半死不活地吊着一口气,像个得了肺痨的老头,每天咳出几匹布,也咳出我们这些年轻人大把的青春。
我的青春,闻起来就是机油、棉絮和食堂白菜汤混合的味道。
直到那一天,我看见了王厂长他那个在外面当“倒爷”的儿子,王兵。
他穿着一件屁股后面带个外国牛头标的裤子,头发抹得锃亮,像刚被牛舔过。
最扎眼的,是他腰上那个黑色的、巴掌大的小盒子。
我们正蹲在车间门口抽烟,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又泡汤了。
突然,王兵腰间的黑盒子“哔哔哔”地响了起来。
那声音,尖利,清脆,像一把小刀,瞬间划破了我们周围沉闷的空气。
所有人的目光,“唰”地一下全射了过去。
王兵不紧不慢地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,用脚尖碾了碾。
他单手解下那个小盒子,看了一眼上面那行红色的数字,嘴角一撇,带着那种我们这辈子都学不来的潇-洒。
“操,催命呢。”
他嘟囔了一句,然后对我们这群土包子扬了扬下巴,转身就朝厂门口的大哥大走去。
那一刻,我手里的“红梅”烟,突然就不香了。
我死死盯着他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,和他腰间那个随着步伐一晃一晃的黑盒子。
那玩意儿叫BP机,也叫寻呼机。
在1995年,那不是一个通讯工具。
那他妈的是身份,是地位,是把“牛逼”两个字刻在脑门上的招牌。
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咆哮。
我也要搞一个。
我必须搞一个。
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,掉进了我贫瘠又焦躁的心里,然后以一种蛮不讲理的速度,疯狂地生根发芽。
我女朋友小娟,在百货大楼当售货员。
她长得好看,眼睛像秋天的湖水,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我俩感情不错,但她爸妈,尤其她爸,一个在粮食局坐办公室的老干部,正眼都没瞧过我。
“小李啊,年轻人,在厂里好好干,争取当个先进。”
他每次见我,都用这种给我上政治课的口气说话。
翻译过来就是:你个穷小子,配不上我女儿。
我把想买BP机的想法跟小娟说了。
她在柜台后面,正用鸡毛掸子掸着玻璃上的灰,听完我的话,手停在了半空中。
“你疯啦?李伟!”
她压低了声音,但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全是震惊。
“那玩意儿要多少钱?三千!你一个月工资多少?三百五!”
“你得不吃不喝攒一年!”
我梗着脖子。
“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
“你想什么办法?你去抢啊?”她有点急了,“咱俩攒点钱,以后结婚买个大彩电,买个冰箱,不比那个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强?”
我没说话,心里却憋着一股火。
你不懂。
你不懂王兵解下BP机时,我们那帮工友羡慕得发绿的眼神。
你不懂你爸看我时,那种轻描淡写的鄙夷。
我需要的不是大彩电,不是冰箱。
我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我直起腰杆的东西。
那个“哔哔”作响的小盒子,就是我的腰杆。
从那天起,我像着了魔。
上班的时候,别人在磨洋工,我在琢磨怎么搞钱。
下班了,别人去录像厅看周润发,我去家电维修铺当学徒,偷师学艺。
我们车间的马师傅,是个老电工,手艺好,就是人懒。
我天天“马师傅长,马师傅短”地伺候着,烟一根接一根地递,茶一杯接一杯地倒。
不出一个月,修个电风扇、接个收音机线路的活儿,我基本都摸清了。
我开始接私活。
街坊邻居谁家电器坏了,我拎着个破工具包就上门。
收钱不多,五块、十块,但架不住积少成多。
我的手上,机油味还没散干净,又添了松香和焊锡的味道。
每天晚上,我把那些攒下来的、带着汗臭和油污的零钱摊在床上,一张一张地数。
五十,一百,三百……
数字往上涨的速度,慢得像蜗牛爬。
而我心里的那团火,却越烧越旺。
我变得越来越抠门。
跟小娟约会,我连一瓶一块五的“健力宝”都舍不得买。
我们在公园里坐着,一人一根五毛钱的冰棍,我都能嘬半个小时。
小娟看我的眼神,慢慢从心疼,变成了不理解。
“李伟,你至于吗?”
“你不懂。”
又是这三个字。
这三个字像一堵墙,慢慢隔在了我们中间。
我开始跟厂里的兄弟借钱。
“强子,借我一百,下月发工资就还。”
“斌子,手头宽裕不?挪两百应应急。”
一开始,大家还都挺仗义。
但次数多了,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
那种躲闪,那种敷衍,比直接拒绝还伤人。
我不管。
我的眼里只有那个数字:三千。
还差一千二。
我把主意打到了我爸妈身上。
我爸,一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,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
我妈,家庭妇女,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。
我找了个周末回家,磨蹭了半天,才吞吞吐吐地开了口。
“爸,妈,我……我想跟你们借点钱。”
我爸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,闻言,把报纸放了下来。
“借钱?你要干啥?”
“我……我想做点小生意。”我撒了谎,我不敢说实话。
我妈从厨房里走出来,手里还拿着把葱。
“做什么生意?你不是在厂里干得好好的吗?”
“厂里那点死工资,能有什么出息。”我的口气有点冲。
我爸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“什么叫死工资?我和你妈就靠着死工资把你拉扯大的!”
“时代不一样了!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,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你们还守着那套老思想!”
空气瞬间凝固了。
我妈眼圈红了,拿着葱的手微微发抖。
我爸死死地盯着我,嘴唇哆嗦着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最后,他从卧室的床头柜里,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,一层一层打开。
里面是五十、一百的,一沓子旧钞票。
“这是一千块钱,家里所有的积蓄了。”
他把钱拍在桌上,声音嘶哑。
“你拿去。要是赔了,就当我没你这个儿子。”
我抓起那沓钱,那钱上仿佛还带着我爸的体温,烫得我手心发麻。
我没敢看他们的眼睛,狼狈地逃出了家门。
那一千块钱,加上我自己的,还有东拼西凑借来的,终于凑够了三千。
我揣着那沓厚厚的、凝聚了我所有尊严和不堪的钞票,直奔市里最大的通讯器材商店。
店里灯火通明,玻璃柜台擦得一尘不染。
穿着西装的售货员,看我的眼神,就像在看一个从乡下来的穷亲戚。
我懒得理他。
我指着柜台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台摩托罗拉BP机,用我这辈子最洪亮的声音说:
“这个,给我拿一个。”
售货员愣了一下,随即换上了一副职业化的假笑。
“先生,这款是‘Bravo Plus’,中文名叫‘精英’,三千二百八,不讲价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妈的,涨价了?
我把那沓皱巴巴的钱掏出来,拍在柜台上。
“我只有三千。”
售-货员的假笑凝固了,嘴角撇了撇。
“那不好意思,先生。”
我当时血就冲上了头。
所有的委屈,所有的辛苦,所有的屈辱,在那一刻全爆发了。
“你他妈什么意思?看不起人是吧?”
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带。
“我告诉你,今天这BP机,三千块,我拿定了!”
店里的经理闻声赶了过来。
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,看着挺斯文。
他把我俩拉开,了解了情况,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:
“这位小兄弟,别激动。这样,看你也是真心想买,我做主,给你抹个零头,三千二,图个吉利。”
我盯着他,他也盯着我。
我知道,这是他的底线了。
我从兜里,掏出我妈给我坐公交车的一块钱,又从另一个兜里,掏出我准备买包烟的五块钱,再加上我所有的钱,还是不够。
那种感觉,就像你拼尽全力跑完了万米长跑,却发现终点线被人往后挪了一百米。
绝望。
就在我准备放弃,准备接受所有人的嘲笑时,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“剩下的,我帮他付了。”
我回头。
是小娟。
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,眼睛红红的,手里攥着一个信封。
她把信封里的钱倒出来,都是些十块、二十的零钱,凑了一百多。
“这是我这个月的奖金。”
她又从手腕上,褪下一个银镯子。
“这个,是我妈给我的,应该能当点钱。”
她把镯子和钱一起推到柜台上,看着那个经理,眼神倔强。
“够了吗?”
我当时,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我看着小娟,看着那个银镯子,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小丑。
一个彻头彻尾的,无可救药的。
最终,那个经理大概是被我们俩这副穷酸又执拗的样子打动了。
他叹了口气,把银镯子推了回来。
“算了算了,当我今天开张做善事了。三千块,拿走。”
BP机到手了。
黑色的塑料外壳,沉甸甸的,带着一种工业时代特有的冰冷质感。
我把它别在我的工装裤腰带上,那个位置,我之前演练过无数次。
不高不低,正好是坐下时不会硌着,站起来又最显眼的地方。
走出商店,阳光有点刺眼。
小娟一直没说话。
我清了清嗓子,想说点什么。
“小娟,那钱……还有你的镯子,我以后……”
“李伟。”她打断了我,“你高兴吗?”
我愣住了。
我看着手里的BP机,又看看她。
我应该高兴的。
我费了那么大的劲,付出了那么多代价,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?
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闷得慌。
“我……”
“你高兴就好。”
她说完,转身走了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,第一次觉得,她离我那么远。
但这种感觉,很快就被BP机带来的虚荣感冲散了。
第二天,我揣着BP机去上班,感觉整个纺织厂的路都变宽了。
我走路的姿势都变了,腰杆挺得笔直,脚步迈得四平八稳,生怕别人看不见我腰上那个黑色的“精英”。
果然,刚进车间,就被人围住了。
“我操,伟哥,你发财了?”
“摩托罗拉!精英!跟王兵那小子的一样啊!”
“伟哥,让摸摸呗?”
我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,脸上故作平静,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
“瞎嚷嚷什么,不就一个BP机嘛,大惊小怪。”
我嘴上这么说,却慢条斯理地把它解下来,递到他们手里,让他们挨个传看。
马强,就是那个平时最爱拍马屁的家伙,也凑了过来。
他眼神里全是嫉妒,嘴上却酸溜溜的。
“哟,李伟,行啊。这玩意儿一个月服务费就得好几十吧?养得起吗?”
我斜了他一眼。
“不劳你操心。”
那几天,是我人生中最“辉煌”的日子。
我吃饭的时候,故意把BP机放在饭桌上。
我跟人说话的时候,总是不经意地撩起衣服,露出腰间的它。
我甚至花钱,让我邻居家的小孩,隔三差五地给我呼一下。
内容都是我自己编的。
“李总,城西那批货到了,请速回电。”
“伟哥,晚上‘皇都’歌舞厅,老地方见。”
每当“哔哔”声响起,我都会在众人的注视下,从容地拿起BP机,看一眼,然后皱着眉头,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。
那感觉,爽!
爽得我快忘了自己是谁了。
小娟还是不怎么理我。
我呼她,她也不回。
我去百货大楼找她,她也总是说忙。
我有点烦躁。
我觉得她不可理喻。
我这么努力,这么有上进心,不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?
她怎么就不懂呢?
机会很快就来了。
厂里要评选“青年技术标兵”,只有一个名额。
谁评上了,不仅有奖金,还有机会送去市里进修,回来就能提个小组长。
我和马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
马强那小子,技术不咋地,但嘴甜,会来事,天天围着车间刘主任屁股后面转。
刘主任是个老油条,就吃这一套。
我知道,光靠技术,我肯定争不过他。
我得想点别的招。
我的目光,落在了腰间的BP机上。
评选前一天,刘主任来车间视察。
我算准了时间,让邻居家小孩给我呼了一个。
“哔哔哔——”
声音在嘈杂的车间里,依然那么醒目。
刘主任果然看了过来。
我装作没听见,继续埋头干活。
旁边的工友推了我一把:“伟哥,你BP机响了!”
我这才“恍然大悟”,一脸“抱歉”地对刘主任笑了笑。
“不好意思啊刘主任,朋友找。”
我拿起BP机,看了一眼,然后故意把声音放大了一点,自言自语道:
“又是工商局的张科长,催着吃饭呢,真烦人。”
我看到,刘主任的眼神明显变了。
那种审视中,带了一丝好奇和……敬畏?
马强在一旁,脸都绿了。
我心里暗爽。
小子,跟我斗?你还嫩了点。
那天下午,结果就出来了。
青年技术标兵,是我。
马强气得脸都变形了,当着所有人的面,把手里的扳手狠狠摔在地上。
“凭什么!我不服!”
刘主任背着手,慢悠悠地走过来。
“马强,注意你的态度。”
他顿了顿,看了一眼我腰间的BP机,意有所指地说:
“李伟同志,不仅技术过硬,社会关系也广,思想也比较……与时俱进。这样的人才,才是我们厂未来需要的。”
我赢了。
靠着一个塑料盒子,和一句谎言。
我拿着奖状和三百块钱奖金,第一时间就跑去找小娟。
我想让她看看,我不是在胡闹。
我买BP机,是有用的。
它能给我带来荣誉,带来地位。
我把奖状塞到她手里。
“看见没?我评上标兵了!刘主任亲口说的,我是人才!”
小娟看着那张红色的奖状,没什么表情。
“就因为你那个BP机?”
“那当然了!”我得意忘形,“你不知道马强那孙子当时的表情,跟吃了屎一样!我跟你说,这玩意儿就是……”
“李伟。”
她又打断了我。
“你还记得你当初学维修,是为了什么吗?”
我愣住了。
“为了……为了攒钱买BP机啊。”
“不是。”她摇了摇头,眼睛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伤,“你忘了。你刚开始学的时候,跟我说,你想学一门真本事,以后就算厂子倒了,我们也能靠手艺吃饭。”
我的心,像是被针扎了一下。
是啊。
我好像……真的忘了。
我忘了那些趴在油腻腻的桌子上,对着电路图研究到半夜的日子。
我忘了第一次修好邻居家的收音机,对方递给我五块钱时,我心里那种踏实的成就感。
我所有努力的初衷,都已经被那个“哔哔”作响的黑盒子给吞噬了。
“你变了,李伟。”
小娟的声音很轻。
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
那天,我们不欢而散。
我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火,觉得她就是看不得我好。
女人嘛,头发长见识短。
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等我以后当了官,发了财,她就知道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了。
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我的BP机。
我把它当成了我的战袍,我的武器。
我去跟别的车间协调工作,先把BP机往桌上一拍。
我去仓库领料,对那些爱答不理的保管员,也总是不经意地亮出我的“精英”。
效果出奇的好。
所有人都对我客气了三分。
他们不再叫我“小李”,而是叫“李师傅”,甚至是“伟哥”。
我飘了。
我真的以为,自己成了个人物。
我开始幻想,自己被送到市里进修,学成归来,当上小组长,然后是车间副主任,主任……
迎娶小娟,让她爸对我刮目相看。
人生巅峰,仿佛触手可及。
然而,生活这个编剧,从来不按你的剧本走。
它最擅长的,就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,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那天,是个周六。
我跟几个所谓的“朋友”,其实就是一些被我的BP机吸引过来的酒肉之交,在外面喝酒。
酒桌上,我又开始吹牛。
从厂里的人事关系,吹到市里的经济形势,仿佛我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。
BP机就放在我手边,像个忠诚的卫士。
为了显示我的业务繁忙,也为了不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呼叫打扰,我把它调成了震动。
这是“精英”款才有的高级功能。
我觉得这样更有范儿。
一个真正的大人物,是不会让“哔哔”声轻易打断自己的谈话的。
我们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。
酒喝了不少,牛也吹得差不多了。
我感觉裤腰带上的BP机震动了好几次。
我拿起来看了一眼,都是些不认识的号码,或者是一些广告信息。
“李总,新到一批钢材,价格优惠。”
我嗤之一鼻,随手就把BP机扔回桌上。
“妈的,现在这骗子,都这么先进了。”
朋友们纷纷附和,夸我见多识广,火眼金睛。
我又喝了一杯,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。
晚上回到家,已经快八点了。
家里黑着灯,没人。
我有点奇怪,我妈平时这个点,肯定在家看电视。
我打开灯,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。
是我邻居张婶写的,字歪歪扭扭。
“小伟,看到速去市一院!你爸出事了!”
我的酒,瞬间醒了一半。
我爸出事了?
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,拦了辆出租车,直奔市一医院。
车上,我掏出BP机。
我看到,上面有十几个未读信息。
全都是同一个号码。
是我家的电话号码。
从下午两点开始,每隔十分钟,就呼我一次。
后面还有几条是张婶家的。
“速回电,你爸不行了!”
“李伟你死哪去了!快来医院!”
“你爸在抢救室,见最后一面!”
最后一面的……
我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炸了。
我死死地攥着那个BP机,那个曾经带给我无限荣耀和虚荣的黑盒子。
此刻,它冰冷得像一块铁,硌得我手心生疼。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,抢救室的灯,已经灭了。
我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,头发凌乱,像是一瞬间老了十岁。
小娟陪在她身边,眼睛肿得像核桃。
我冲过去。
“妈!我爸呢?”
我妈抬起头,看到我,眼神空洞。
她没有哭,也没有骂我。
她只是看着我,然后,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。
“啪!”
清脆,响亮。
整个走廊的人都看了过来。
我的脸,火辣辣地疼。
但远不及我心里的万分之一。
“你爸……走了。”
我妈的声音,像从地底下飘出来一样,没有一丝温度。
“中午在家里,突发心梗。我让你张婶给你打电话,打不通。我让她给你发BP机,发了几十条,你也没回。”
“医生说……要是早送来半个小时……或许还有救……”
“李伟……你当时……在干什么啊?”
我当时在干什么?
我在喝酒。
我在吹牛。
我把那个能救我爸命的BP机,调成了震动,扔在桌上,因为它打扰了我吹牛逼。
我看着我妈绝望的脸,看着小娟鄙夷的眼神。
我突然想笑。
笑我自己,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缺。
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透支了所有的亲情和友情,换来了这么一个玩意儿。
我以为它能给我带来身份,带来地位,能让我成为人上人。
结果,它在我爸最需要我的时候,让我变成了一个失联的、不孝的。
我把它从腰上解下来,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“哐当!”
黑色的塑料外壳摔得四分五裂,露出了里面复杂的电路板和零件。
它再也不会响了。
就像我爸的心跳,再也不会有了。
我跪在我妈面前,嚎啕大哭。
我爸的葬礼,很简单。
来的人不多,都是些老街坊和厂里的老同事。
王厂长也来了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节哀。
我看见他儿子王兵,站在不远处,腰上那个同款的BP机,格外刺眼。
我没看见马强。
后来听人说,他顶替了我去市里进修的名额。
是刘主任特批的。
我不在乎了。
这一切,都跟我没关系了。
小娟的爸爸,那个一直看不起我的粮食局老干部,也来了。
他没跟我说什么大道理。
只是在临走的时候,递给我一个信封。
“这是我和你阿姨的一点心意,给你妈买点营养品。”
他看着我,眼神很复杂。
“小伟,人这一辈子,总要摔个大跟头,才能长大。”
“别趴在地上不起来。”
我拿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,半天说不出话。
这个我一直想用BP机去“征服”的老人,在我最落魄的时候,给了我一份最实在的温暖。
真是讽刺。
葬礼过后,我把自己关在家里,整整一个星期。
我不洗脸,不刮胡子,像个野人。
我妈默默地把饭菜放在我门口,又默默地端走。
她不骂我,也不劝我。
她只是用一种巨大的悲伤,把我包裹起来,让我无处可逃。
我每天都在想,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喝酒。
如果那天我没有把BP机调成震动。
如果我早半个小时接到电话。
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?
可生活没有如果。
一个星期后,小娟来了。
她帮我收拾了屋子,把窗户打开,让阳光照进来。
屋子里那股发霉的味道,散了一点。
她坐在我对面,看着我。
“李伟,我们分手吧。”
我心里一抽,但并不意外。
“好。”
我只说了一个字。
我还有什么资格留住她?
“我爸……帮我介绍了个对象,在银行上班,人挺老实的。”
“挺好。”
“李伟……”她欲言又止,眼圈又红了,“你……以后好好的。”
“嗯。”
她走了。
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,和我爸去世那天一样。
只是这一次,我知道,她是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
我的世界,在短短半个月里,彻底崩塌了。
我失去了父亲,失去了前途,也失去了爱情。
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,就是那个已经被我摔碎的,叫“精英”的BP机。
我回去上班了。
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,都带着同情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……幸灾乐祸?
马强已经去市里进修了,听说回来就是小组长。
刘主任见到我,也只是点点头,像不认识我一样。
我成了车间里的透明人。
我不再是那个腰里别着BP机,走到哪都前呼后拥的“伟哥”。
我又变回了那个满身机油味,一个月挣三百五的“小李”。
不,甚至还不如从前。
从前的我,虽然穷,但心里有股劲儿,有盼头。
现在的我,像个被抽了脊梁骨的癞皮狗,每天行尸走肉。
我开始酗酒。
每天下班,就去街边的小饭馆,一瓶二锅头,一盘花生米,能坐到半夜。
我喝醉了就哭,哭我爸,哭小娟,哭我那操蛋的人生。
饭馆老板是个实在人,总是在我喝得不省人事的时候,把我架回我家。
我妈看着我这副鬼样子,只是默默地流泪,帮我擦脸,盖被子。
有一天,我又喝多了,在家里耍酒疯。
我把我爸的遗像给打了。
相框碎了一地。
我妈冲过来,疯了一样地打我,捶我。
“你这个!你对得起你爸吗!你对得起我吗!”
“他走了,你也要跟着作死是不是!你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!”
她哭得撕心裂肺。
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,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,看着她绝望的眼神。
我突然就清醒了。
我爸已经走了。
我不能再让我妈也对我失望。
我跪在地上,捡起我爸的遗像,用袖子把上面的玻璃碴子一点一点擦干净。
“妈,我错了。”
“我真的错了。”
从那天起,我再也没喝过一滴酒。
我把家里欠的钱,一笔一笔地记下来。
我开始拼命地工作。
厂里最脏最累的活,没人愿意干的,我抢着干。
下了班,我继续去接私活修电器。
我的手艺越来越好,找我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我不再是为了虚荣,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挣钱,还债,养家。
我话变得很少。
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回家陪我妈。
我们俩一起看电视,一起包饺子,日子过得平淡,但很安稳。
一年后,我还清了所有的债。
我还用攒下的钱,给我妈买了一台新的洗衣机。
我妈看着那台崭新的“小天鹅”,摸了又摸,眼圈都红了。
“儿啊,你长大了。”
我笑了笑,心里酸酸的。
是啊,长大了。
用我爸的一条命,和我最爱的人离开,换来的成长。
这代价,太大了。
又过了两年,国营厂改革,我们厂最终还是没撑住,倒闭了。
工人们都拿了一笔遣散费,各自谋生。
马强进修回来,小组长还没当热乎,就下了岗。
听说他后来去南方打了几年工,也没混出什么名堂。
我用那笔遣散费,加上我修电器攒的钱,在市中心租了个小门面,开了一家家电维修店。
我的店,名字就叫“实在维修”。
因为手艺好,收费公道,从不坑人,生意慢慢地好了起来。
后来,我结了婚。
我老婆是我一个客户介绍的,是个小学老师,人很贤惠,不嫌我穷,也不嫌我没文化。
我们有了一个儿子,很可爱。
日子就像温水,不烫,但暖和。
有一次,我带着老婆孩子去逛商场。
路过一个手机柜台,我看到现在的小年轻,人手一个苹果手机。
我儿子指着那个亮晶晶的玩意儿,吵着要。
我老婆在一旁哄他。
我看着那些年轻人,他们低着头,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划着。
他们的世界,都在那个小小的盒子里。
我突然就想起了我的那个BP机。
想起1995年的那个夏天。
想起那个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“牛逼”,而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的二十三岁的自己。
几十年过去了。
BP机早就被淘汰了,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
大哥大,小灵通,诺基亚……一代又一代的通讯工具,来了又走。
现在的年轻人,可能都不知道BP机是什么东西了。
他们追逐着更新的、更酷的、更能代表身份的东西。
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
时代在变,技术在变,但人性里那些虚荣、欲望和愚蠢,好像从来没变过。
前几年,我回老家,收拾我爸妈的老房子。
在一个旧箱子的角落里,我翻出了那个被我摔碎的BP机。
外壳裂了,屏幕也碎了,但那个摩托罗拉的标志,还清晰可见。
我把它拿在手里,很轻。
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沉重感。
我看着它,就像看着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。
一个曾经让我爱过、恨过、疯狂过,也让我成长过的老朋友。
我笑了笑。
95年我花三千买个BP机,觉得自己很牛。
现在看来,我就是个傻缺。
一个彻头彻尾的,无可救药的,但是……终于长大了的傻缺。
我把它重新放回箱底,和那些泛黄的旧照片,和我那段回不去的青春,放在了一起。
然后,我关上箱子,走出了老屋。
外面阳光正好。
我儿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咯咯地笑。
我老婆在厨房里喊我。
“李伟,吃饭了!”
“哎,来了!”
我应了一声,大步走了过去。
那是我人生中,走得最踏实的一段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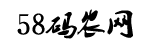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