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哈,这回忆太具体了!93年,那可是改革开放后通讯开始普及,但还属于“奢侈品”的时代。
"五百块买BP机:" 在93年,五百块人民币绝对是相当一笔不小的数目,尤其是在农村。这说明你当时可能家境不错,或者特别有眼光,或者就是纯粹喜欢这种“新潮玩意儿”。拥有一台BP机,在当时确实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能收到信息,尤其是在信息闭塞的村里,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这绝对是当时的“标配”通讯工具,代表着“会联系”、“有信息”。
"后来换了大哥大:" BP机只能接收信息,还不能通话,且覆盖范围有限。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,大哥大(早期模拟手机)出现了,可以随时随地通话,真正实现了移动通讯的自由。从BP机换到大哥大,是通讯时代的又一次飞跃,也是个人生活品质提升的体现。这在当时更是引起了轰动,代表着更强的社交能力和更强的经济实力。
你这段经历,完美地记录了中国移动通讯从无到有、从模拟到数字、从固定到移动的早期发展历程,也反映了个人生活水平的变迁。这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“老时光”!
你还有其他关于那个年代的有趣回忆吗?
相关内容:
1993年的夏天,热得像个发了疯的婆娘,逮谁跟谁急眼。
我们陈家村的土路,被日头晒得往上冒白烟,踩一脚都烫得人直蹦。
村里的后生们,要么在田里撅着屁股伺候那几亩薄地,要么就光着膀子在村口大槐树下,摇着破蒲扇,骂着天,说着荤话。
我叫陈浩,那年二十。
我不一样。
我不想跟他们一样。
我心里揣着一团火,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
这火,是城里人点的。
那天我跟着我爹去县城卖粮食,在最大的“宏发商场”门口,看见一个穿白衬衫、夹个黑皮包的男人。
他那白衬衫,白得晃眼,不像我们村的,洗几次就发黄发灰。
他没急着走,就站在门口,像是在等什么。
突然,他腰上别着的一个黑匣子,“哔哔哔”地响了起来。
那声音,尖利,急促,像是一道命令。
周围所有人的目光,“唰”地一下全射了过去。
男人不慌不忙,把那黑匣子从腰上解下来,看了一眼,然后就近找了个小卖部,往柜台上拍了一块钱。
“老板,打电话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,但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派头。
我爹拉了我一把,小声说:“别看了,那是BP机,大老板才有的玩意儿。”
BP机。
这三个字,像三颗钉子,狠狠钉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从那天起,我就魔怔了。
晚上睡不着,眼前晃悠的就是那个黑匣C子,耳朵里响的就是那阵“哔哔哔”。
那不是声音,那是身份,是脸面,是走出这片穷土地的通行证。
我要一个。
我必须得有一个。
我跟爹妈提了一嘴。
我爹正蹲在门槛上抽他的旱烟,听完,烟锅子在鞋底上“梆梆”磕了两下。
“五百块?你咋不去抢?”
他眼皮都没抬,“咱家一年到头,刨去吃喝开销,能剩下几个五百块?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啥?”
我娘在旁边纳鞋底,叹了口气,“浩子,那不是咱庄稼人该想的东西,安安分分种地,攒钱娶个媳妇,比啥都强。”
安安分分。
我最恨的就是这四个字。
安安分分,就是一辈子跟黄土打交道,活得像地里的一棵蔫吧玉米。
我没再跟他们吵。
我知道,没用。
他们不懂。
他们的世界,就是门口那二亩地,就是村东头那口井。
而我的世界,我想让它变得更大。
钱。
一切都是钱。
我开始疯了一样地攒钱。
白天跟爹下地,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。
晚上村里人聚在一起侃大山,我偷偷跑到后山,给人家挖药材,打零工。
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,血泡变成死皮,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
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。
“陈家这小子,是不是中邪了?”
“是啊,一天到晚不说话,就知道埋头干活,眼睛都发绿。”
尤其是村里的混子头王二狗,他最爱拿我开涮。
他仗着他爹是村支书,整天游手好闲,头发抹得油光锃亮,学城里人穿个喇叭裤,在村里横着走。
那天我在河边洗药材,他晃悠过来,一脚踩在我刚洗好的一堆柴胡上。
“哟,陈浩,又在这儿发财呢?准备攒钱娶哪个村的俊媳妇啊?”
他身后的几个跟屁虫哈哈大笑。
我没抬头,默默地把被他踩脏的药材捡起来,重新洗。
他觉得没趣,蹲下来,凑到我耳边说:“我跟你说,就你这样,累死也还是个泥腿子。你跟我们,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”
我猛地抬起头,死死盯着他。
他被我看得一愣,随即又笑了起来,那笑声里满是轻蔑。
“怎么?不服气?不服气你也去弄个BP机啊,就像城里大老板那样,往腰上一别,多威风!”
他不知道,他这句话,不是在嘲讽我。
他是在给我上弦。
两个月。
整整两个月,我除了吃饭睡觉,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——搞钱。
我把所有攒下的钱,加上跟我最铁的发小张胖子借的一百块,凑了整整五百二十块。
钱用一块破布包着,揣在最贴身的口袋里,鼓鼓囊囊的,像是我的心脏。
我跟爹妈说,去县城给舅舅家帮忙。
他们没怀疑。
我坐上了村里那辆一天一趟的拖拉机,“突突突”地朝着县城奔去。
那条土路,我走了无数遍,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,觉得它是一条通往新世界的光明大道。
还是那家“宏发商场”。
我站在门口,深吸了一口气,走了进去。
里面的冷气吹得我一哆嗦。
卖BP机的柜台在最里面,一个烫着卷发的女售货员,正百无聊赖地涂着红指甲。
她看见我,上下打量了一眼,眼神里带着点嫌弃。
我这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,跟这里确实格格不入。
“同志,买东西?”她问,声音懒洋洋的。
“我……我想看看BP机。”我有点紧张,声音都发颤。
她抬了抬眼皮,指了指玻璃柜台,“都在这儿,自己看。”
我趴在柜台前,像个朝圣者。
摩托罗拉,汉显,数字机……各种各样的黑匣子,静静地躺在红色绒布上,闪着诱人的光。
“这个,多少钱?”我指着一个最普通的数字机。
“五百。”
“能……能便宜点吗?”我鼓起勇气问。
她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“小兄弟,你当这是菜市场买白菜呢?”
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
我没再说话,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,一层一层地打开。
里面是汗津津的、皱巴巴的票子。
有一块的,五块的,十块的,最大的一张是五十的。
我把钱一张一张地铺在玻璃柜台上,小心翼翼地数着。
女售货员的表情变了。
那笑容里的嘲讽,慢慢变成了惊讶,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神情。
五百块钱,对她来说可能不算什么,但她一定能看出来,这些钱,对我意味着什么。
她没再说话,默默地帮我把钱点了一遍。
“够了。”
她从柜台里拿出那个崭新的BP机,放在盒子里,递给我。
“这是说明书,保修单,收好。”
我接过盒子,感觉像接过来一个滚烫的山芋。
我甚至不敢打开看,紧紧地抱在怀里,转身就往外跑。
直到跑出商场,站在大太阳底下,我才敢打开盒子。
黑色的,塑料的,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,沉甸甸的。
我把它拿出来,学着那个白衬衫男人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别在了我腰间的皮带上。
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发光。
回到村里的时候,天已经快黑了。
我故意挺直了腰杆,从村口最热闹的大槐树下走过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像探照灯一样,聚焦在我腰间的那个黑匣子上。
“那……那是啥?”
“好像是……BP机?”
“天爷!陈浩这小子发财了?”
议论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。
王二狗也在。
他嘴里叼着根烟,看到我腰上的东西,烟“啪嗒”一下掉在了地上。
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,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
我没看他,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
我能感觉到,他那嫉妒得快要喷火的目光,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后背上。
爽。
前所未有的爽。
这两个月受的累,吃的苦,在这一刻,全都值了。
我爹妈看见我腰上的BP机,差点没把下巴惊掉。
我爹举起烟杆就要揍我,被我娘死死拦住。
“你个败家子!你哪来这么多钱!”
“我自己挣的。”我梗着脖子。
“挣的?你干啥能挣这么多钱?你是不是去干什么坏事了?”
我懒得解释。
我把BP机解下来,放在桌上,“以后你们有急事找我,就去村头小卖部,打这个号码,我马上就能收到。”
我把BP机的号码,用铅笔写在一张破纸上,拍在桌子上。
他们俩看着那个黑匣C子,像是看一个怪物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从那天起,我在村里的地位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以前见了我爱答不理的大爷大妈,现在隔着老远就冲我笑。
“浩子,出息了啊!”
“浩子,啥时候带我们发财啊?”
我只是笑笑,不说话。
我把腰杆挺得更直了。
BP机成了我的护身符,也是我的名片。
最戏剧性的一幕,发生在一个礼拜后。
村长的老婆半夜突发急病,疼得在床上打滚。
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看了,直摇头,说得赶紧送县医院,晚了就麻烦了。
可那时候,村里连一辆拖拉机都没有,唯一通往外面的路,就是那条漆黑的土路。
全村人都急得团团转。
就在这时候,有人想起了我。
“找陈浩啊!他有BP机,他肯定有办法联系到城里的人!”
一群人呼啦啦地冲到我家,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。
我看着村长那张急得快要哭出来的脸,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
我拿着BP机号码,跑到村头小卖部。
小卖部的王大爷已经被吵醒了,睡眼惺忪地看着我。
我把号码递给他,让他打给我在县城认识的一个跑运输的朋友。
那个朋友,是我卖药材的时候认识的,当时留了电话,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
电话接通了。
我对着话筒大喊,把情况说了一遍。
对方答应马上开车过来。
挂了电话,整个村子的人都围着我,大气都不敢出。
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,远处传来了汽车的灯光和马达声。
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。
村长老婆被顺利地送到了县医院,后来听说,抢救得很及时,人没事了。
第二天,村长提着两瓶酒和一条烟,亲自上门感谢我。
他拍着我的肩膀,说:“浩子,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。以前是我小看你了。”
我爹在旁边,脸上的表情又骄傲又复杂。
他默默地接过酒,没说话,但眼神里,第一次有了对我的认可。
而我,看着桌上的BP机,第一次感觉到,它不只是一个用来炫耀的玩意儿。
它是一种力量。
是一种连接,连接着这个小村子和外面的世界。
而我,就是那个掌握连接的人。
我的BP机,成了村里的“110”。
东家长,西家短,谁家有急事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
我开始变得忙碌起来。
“浩子,我儿子在城里打工,好久没消息了,你帮我呼他一下。”
“浩子,我家的猪病了,你帮我问问县里的兽医站。”
我的BP机,每天都要响上好几次。
每一次“哔哔哔”的声音响起,我都会在众人的注视下,飞奔向村头的小卖部。
那种被需要、被仰视的感觉,让我飘飘然。
王二狗看我的眼神,从嫉妒变成了怨毒。
他开始在背后散布我的谣言。
“切,不就是个传话的吗?牛气什么?”
“听说他那BP机是假的,根本呼不通。”
“他挣的钱,肯定来路不正,不然哪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。”
我懒得理他。
我知道,他越是这样,就越证明他怕了,他输了。
我的心思,已经不在村里这点鸡毛蒜皮上了。
通过BP机,我联系上了越来越多城里的人。
卖药材的李老板,跑运输的张大哥,甚至还有在政府部门上班的小科员。
我的世界,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张。
我发现了一个商机。
我们村后山,有一种野生的山楂,酸甜可口,但因为路不好走,一直没人愿意费劲弄出去卖。
城里人现在生活好了,就喜欢这种纯天然的东西。
我通过BP机联系了李老板,给他寄了点样品。
他尝了之后,大加赞赏,说有多少他要多少,价格好商量。
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。
这是一个机会,一个能让我真正“站起来”的机会。
我不再是那个只会被动接收信息的传话筒,我要成为信息的发布者,规则的制定者。
我开始组织村里的年轻人,上山摘山楂。
一开始,没人愿意跟我干。
他们不相信这玩意儿能换钱。
“浩子,别折腾了,那玩意儿酸得掉牙,谁会买?”
“就是,有那功夫,还不如多锄两亩地。”
我没有多费口舌。
我找到我最好的兄弟,张胖子。
“胖子,你信不信我?”
张胖子憨厚地笑了笑,“浩子,我不知道那玩意儿能不能卖钱,但我信你。”
就这样,我俩带头上了山。
我们干了三天,摘了满满五大袋。
我用张大哥的运输车,把山楂运到了县城,交给了李老板。
李老板当场就点了八百块钱给我。
当我拿着那厚厚一沓钱回到村里时,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,眼睛都直了。
八百块!
这比他们种一年地挣得都多!
“浩子……这……这山楂真能卖钱?”
“浩子,下次去摘,带上我一个呗!”
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谄媚的脸,心里冷笑。
但我没有拒绝。
我知道,想要做大事,光靠我一个人不行。
我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了起来,成立了一个“山货队”,我当队长。
我们分工明确,采摘、筛选、运输,一条龙。
我的BP机,成了指挥中心。
“喂,张大哥吗?明天早上八点,老地方,有两千斤货。”
“李老板,款准备好,我们的人马上就到。”
“哔哔哔”的声音,不再是炫耀的资本,而是生意场上的战鼓。
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。
从山楂,到核桃,再到各种菌菇。
陈家村的后山,成了一座金山。
村里人的腰包,渐渐鼓了起来。
我也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“能人”。
就连王二狗他爹,村支书,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。
“陈浩啊,你可是我们村的致富带头人啊!”
王二狗更是不敢再找我麻烦,看见我都绕着走。
我用挣来的第一笔大钱,把家里的土坯房,翻盖成了三层小楼。
在全村清一色的低矮平房里,我家那栋贴着白色瓷砖的小楼,鹤立鸡鸡群,格外显眼。
我还给爹买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。
当电视里出现彩色画面的那一刻,我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,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
他拍着我的肩膀,连说了三个“好”。
我知道,他终于从心底里,接受了我走的路。
我的爱情,也悄然而至。
她是邻村的,叫翠芬,是她们村的“一枝花”。
我们是在一次赶集的时候认识的。
那天我正在跟一个老板谈生意,腰上的BP机响了。
我跑到电话亭回电话,出来的时候,看见一个姑娘站在我摊位前,看着我留在摊位上的BP机发呆。
她长得很好看,两个大辫子,眼睛像一汪清水。
“这是你的?”她问我。
我点点头。
“你是做什么大生意的吧?”她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。
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。
翠芬是个很淳朴的姑娘,她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,只看到我表面的风光。
她会问我,跑生意累不累。
她会关心我,吃饭了没有。
跟她在一起,我能卸下所有的防备和伪装。
我们的感情,发展得很快。
她会偷偷跑到我们村,给我送她亲手做的布鞋。
我也会买城里最时髦的头花和雪花膏送给她。
在那个年代,我们的恋爱,是全村人羡慕的焦点。
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,把BP机从我腰上解下来,别到她腰上时,她羞红了脸,周围的姑娘们则发出了嫉妒的尖叫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时光。
事业有成,爱情甜蜜,乡亲敬重,父母骄傲。
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但生活,总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,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那一年,南方的水果,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什么香蕉、荔枝、芒果,又便宜又好看。
我们本地的山货,一下子就没了市场。
李老板的电话,一天比一天少。
他每次都唉声叹气:“浩子,不是我不帮你,是现在这行情,实在不行啊。”
我辛辛苦苦从山上弄下来的几千斤核桃,堆在仓库里,慢慢发霉。
村里人开始有怨言了。
“还以为跟着陈浩能发财,这下可好,本都赔进去了。”
“他那BP机,最近怎么不响了?”
“我看他就是个银样镴枪头,中看不中用。”
风言风语,像刀子一样,扎进我的耳朵。
我整夜整夜地失眠,嘴上起了燎泡。
翠芬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
她把她准备做嫁妆的钱,全都取了出来,塞给我。
“浩子,别急,咱们慢慢来,大不了,我们还回去种地。”
我抱着她,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我不能回去种地。
我陈浩,从泥里爬出来,就没想过再回去。
我必须找到新的出路。
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,王二狗,这个我早就忘在脑后的人,又跳了出来。
他不知道从哪儿搭上了一个南方的老板,也开始做起了水果生意。
他开着一辆崭新的“东风”卡车,在村里招摇过市。
车上拉着一箱箱的香蕉和橘子。
他把车停在我家新盖的小楼前,扯着嗓子喊:“卖水果咯!南方的水果,又甜又便宜!”
村里人呼啦啦地围了上去。
他一边卖,一边阴阳怪气地说:“还是城里人的东西好啊,比咱们这山沟沟里的土玩意儿强多了。有些人啊,抱着个破山楂核桃,还当宝贝呢!”
他的眼睛,一直瞟着我家的窗户。
我站在二楼的窗帘后面,拳头捏得咯咯作响。
这是挑衅。
赤裸裸的挑衅。
他不仅抢了我的生意,还要踩着我的脸,告诉所有人,他王二狗,才是这个村的新王。
我不能忍。
我冲了下去。
“王二狗,你什么意思?”
他看到我,笑得更得意了,“我没什么意思啊,陈大老板。我就是卖个水果,服务乡亲,不像某些人,把大家伙都带到沟里去了。”
“你!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
“怎么?想打架?”他把袖子一捋,露出了粗壮的胳膊,“陈浩,我告诉你,时代变了。你那套,过时了!”
他指了指我腰间的BP机,轻蔑地笑道:“还当个宝呢?现在城里真正的老板,早不用这玩意儿了!”
他说着,从他那个油腻腻的皮包里,掏出了一个黑乎乎、像砖头一样的东西。
他把一根长长的天线拔了出来,放在嘴边,大声说:“喂!喂!听得到吗?对,我是王二狗!货到了,钱准备好!”
那东西里,传出了清晰的电流声和对方的回话。
周围的村民,全都看傻了。
我的脑袋,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那是什么?
那是什么东西?
它不用连接电话线,就能直接通话?
“看见了吗?”王二狗把那“砖头”在我面前晃了晃,“这叫‘大哥大’!移动电话!你那玩意儿,只能收个信儿,我这个,能直接谈生意!”
大哥大。
又是一个新名词。
它像一把重锤,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。
我呆呆地看着我腰间的BP机。
它曾经是我的荣耀,我的图腾。
但此刻,在那个叫“大哥大”的怪物面前,它显得那么可笑,那么寒酸,那么……无力。
王二狗说得对。
时代变了。
我被时代,狠狠地甩在了后面。
那晚,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喝得酩酊大醉。
我把那个BP机,从腰上扯下来,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但它只是弹了一下,外壳裂开了一道缝,依然顽固地躺在那里,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和愤怒。
我输了。
输得一败涂地。
王二狗的生意,做得风生水起。
他的卡车,从一天一趟,变成了两天三趟。
他成了村里的新偶像,身边围满了阿谀奉承的人。
而我,成了村里的笑话。
“看,那就是陈浩,以前多威风,现在屁都不是了。”
“听说他媳妇都快跟人跑了。”
这些话,像毒蛇一样,啃噬着我的自尊。
我开始躲着人走,白天不敢出门,只有到了晚上,才敢在村里溜达一圈。
翠芬没有离开我。
她每天都来陪我,给我做饭,安慰我。
“浩子,别听他们瞎说。钱没了,可以再挣。只要我们人好好的,比什么都强。”
可我听不进去。
我是一个男人。
我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失败和屈辱?
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、双眼无神的自己,感到无比的陌生和厌恶。
我必须重新站起来。
我需要一个大哥大。
我需要那个能让我跟上时代,甚至超越时代的武器。
可一个大哥大,要两万多块。
两万块!
那对我来说,是个天文数字。
我把仓库里剩下的山货,贱卖了出去,只换回来几百块钱。
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盘算了一遍,就算全卖了,也凑不够一个零头。
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。
那种无论你怎么挣扎,都看不到一丝光亮的绝望。
就在这时,张胖子找到了我。
他看着我颓废的样子,叹了口气,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。
“浩子,这是我全部的家当,三千块。我知道不够,但你先拿着应急。”
我看着他,眼圈红了。
“胖子,这钱我不能要。”
“你不要,就是不认我这个兄弟!”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,“我相信你,你一定能东山再起。”
翠芬也把她家唯一的一头老黄牛卖了,换了一千多块钱,塞给了我。
“浩子,这是我的心意。你别嫌少。”
我拿着这些浸透了亲情和友情的钱,感觉有千斤重。
我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。
为了他们,我也必须拼一次。
我带着这四千多块钱,再次踏上了去县城的路。
这一次,我的心情,比上一次买BP机时,要沉重一百倍。
那一次,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。
这一次,是背负着所有人的期望,去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豪赌。
我找到了以前合作过的李老板。
他看到我,也是一脸的惋惜。
“浩子,你的事我听说了。那个王二狗,就是个小人。”
我没心情跟他聊这些,我开门见山:“李老板,我想跟你借钱。”
李老板愣了一下。
“借钱?借多少?”
“两万。”
他倒吸了一口凉气,“浩子,你疯了?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?”
“我要买大哥大,我要做生意,我要翻本。”我的语气,斩钉截铁。
李老板沉默了。
他抽了半根烟,看着我,眼神很复杂。
“浩子,不是我不帮你。两万块,不是个小数目。而且,现在的生意不好做,你拿着这个钱,万一又赔了……”
他的话没说完,但我懂了。
他不信我了。
也是,一个失败者,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再信任你呢?
我从李老板那里出来,感觉天都灰了。
我在县城的街上,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路过邮电局门口,我看到了大哥大的广告。
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,举着大哥大,笑得无比自信。
广告词写着:“一机在手,掌控所有。”
我站在这块巨大的广告牌下,像个傻子一样,看了很久很久。
难道,我陈浩这辈子,就真的这样了吗?
我不甘心。
我真的不甘心!
一个疯狂的念头,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。
我去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——县里的地下赌场。
那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带我认识的,他说那里来钱快。
我以前对这种地方,是嗤之以鼻的。
但现在,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赌场里乌烟瘴气,人声鼎沸。
红了眼的赌徒们,围在桌子前,声嘶力竭地喊着“大!小!”。
我攥着那四千多块钱,手心全是汗。
我告诉自己,就玩一把。
赢了,我就有本钱。
输了,我就认命。
我把所有的钱,都押在了“大”上。
骰子在碗里,发出清脆又令人心悸的响声。
我的心脏,快要跳出嗓子眼。
“开!三四五,大!”
我赢了。
那一瞬间,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。
我没有收手。
我知道,一旦收手,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勇气了。
我继续押。
大。
还是大。
我像疯了一样,把赢来的钱,一次又一次地全部押上去。
周围的人,都开始跟着我下注。
我成了赌场的焦点。
一个小时后,我面前的筹码,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我数了数,三万多。
够了。
我抓起筹码,跌跌撞撞地跑去兑换处。
赌场的老板,一个脸上带刀疤的男人,拦住了我。
“小兄弟,手气不错啊。不继续玩了?”
“不玩了。”我的声音都在抖。
他笑了笑,没再拦我。
我换了钱,揣在怀里,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外面的空气,是那么的新鲜。
我靠在墙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我赢了。
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我感觉自己像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。
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那赌场一眼。
第二天,我揣着三万块钱,走进了邮电局。
我用一种近乎报复性的快感,买下了那个最贵、最新款的摩托罗拉大哥大。
办入网手续,选号码,花了两万五。
当营业员把那个沉甸甸的“砖头”交到我手里时,我的手,依然在抖。
但这一次,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因为激动。
我回来了。
我陈浩,又回来了。
我拿着大哥大,走在县城的大街上。
我把它举到耳边,虽然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,但我依然装作在打电话的样子。
“喂!对!是我!”
所有路过的人,都向我投来或羡慕,或惊讶的目光。
我知道,这种感觉,又回来了。
但这一次,我心里很平静。
我不再是为了炫耀。
我知道,这东西,是我翻身的唯一希望。
我没有立刻回村。
我知道,仅仅拿着一个大哥大回去,除了能让王二狗难堪一下,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
我要做的,是带着真正的生意回去。
我利用剩下的钱,在县城租了一个小门面。
然后,我开始用我的大哥大,疯狂地打电话。
我打给所有我认识的人。
南方的,北方的,城里的,乡下的。
我告诉他们,我陈浩,现在有了一个全新的生意平台。
我不再局限于山货。
服装、电器、建材……只要能挣钱的,我都做。
我的大哥大,成了我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办公室。
它不像BP机,需要等待,需要中转。
它直接,高效,充满了力量。
我可以在田埂上,跟广州的老板谈几十万的订单。
我可以在颠簸的货车里,指挥深圳的工厂发货。
信息,第一次如此直接、如此迅速地掌握在我的手里。
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将军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。
我的生意,像滚雪球一样,越做越大。
一个月后,我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,回到了陈家村。
车子开到村口,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
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,围着我的车,像是看什么稀罕物。
王二狗也来了。
他那辆“东风”卡车,跟我的桑塔纳比起来,就像个土老帽。
他看着我从车上下来,手里拿着大哥大,脸上的表情,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
我走到他面前,笑了笑。
“二狗,听说你水果生意不错啊。”
他没说话,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
我拿出大哥大,拨了个号码。
“喂,刘经理吗?我陈浩。对,我订的那十个货柜的进口水果,什么时候能到港?好,好,我知道了。”
我挂了电话,拍了拍王二狗的肩膀。
“以后,想做水果生意,可以来找我。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,我给你个批发价。”
说完,我不再看他,在村民们敬畏的目光中,走回了家。
我知道,这一局,我赢了。
而且,赢得彻彻底底。
我没有报复王二狗。
因为,他已经不配做我的对手了。
我的战场,早已不在这个小小的陈家村。
我把爹娘接到了县城,给他们买了套大房子。
我也跟翠芬,举行了一场全县最风光的婚礼。
婚礼那天,我那个曾经被我摔坏的BP机,不知道被谁翻了出来,摆在了桌子上。
它静静地躺在那里,外壳上还有一道裂纹。
我看着它,心里百感交集。
是它,开启了我的梦想,给了我最初的荣耀和自信。
也是它,让我经历了最惨痛的失败,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时代的浪潮。
它就像我青春的纪念碑。
如今,我的大哥大,已经换了好几代。
从笨重的“砖头”,到小巧的翻盖手机,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。
科技在变,时代在变,我的生意也在变。
我从一个小小的“倒爷”,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公司的企业家。
陈家村,也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。
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,通了水泥路,年轻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。
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,在那个年代,一个“哔哔哔”作响的BP机,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,意味着什么。
那是一个梦想的开端。
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。
有时候,夜深人静,我还是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。
想起那个为了五百块钱,拼尽了全身力气的少年。
想起他把BP机别在腰上时,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骄傲。
我拿起手机,屏幕上闪烁着各种信息和数据。
我知道,我已经回不去了。
我们所有人都被时代的洪流,推着向前走。
无法回头。
也无需回头。
只是偶尔,我会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。
嘿,陈浩。
你小子,当年真挺牛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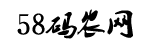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