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和恐惧的情景。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锁着的房间里,而且感觉到了窒息的危险,这无疑是一种极其痛苦和危急的体验。
在这种紧急情况下,你应该立刻采取行动:
1. "立刻尝试呼救:" 如果可能,立刻大声呼喊,看看家里其他人是否在附近能听到。或者尝试用手机联系家人。
2. "检查门窗:" 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完全被困,有没有其他可以打开的出口(比如通风窗、紧急出口等)。
3. "保持冷静:" 尽量深呼吸,虽然可能很难,但恐慌只会加剧窒息感。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,想办法解决问题。
4. "寻找其他钥匙或开锁工具:" 看看钥匙掉落的地方附近有没有其他钥匙,或者家里是否有备用的钥匙、小刀、钳子等可以用来撬锁的工具(请确保这样做不会损坏门或伤到自己)。
5. "寻求外部帮助:" 如果自己无法打开门,并且情况紧急,可以尝试拨打紧急电话(如中国的110或120),说明情况。
请记住,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情况下,不要犹豫,立刻采取行动寻求帮助。
如果你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情景,或者只是想表达你的感受,我在这里愿意倾听。
相关内容:
我推开门,那股味儿就冲了出来。不是灰尘味儿,是甜的,腻的,带着点铁锈腥气,闷了很久突然见光的那种。我胃里一阵翻腾。
公公的咆哮从背后炸开:“谁让你开的!滚出去!”
他冲过来,想把我拽出去。我手里攥着那把黄铜钥匙,刚才从他裤兜里掉出来的,还带着他的体温。我躲开了,手指着里面:“那是什么?”
书房地上,摊着一块深红色的绒布,上面摆着东西。光线暗,我看不清。
“关你屁事!这是我家!书房我说了算!”他脸涨成猪肝色,伸手来抢钥匙。他力气真大,指甲抠进我手腕里。疼。
“你家?”我甩开他,声音我自己听着都陌生,尖得吓人,“房贷是我和杨健在还!物业费水电费是我在交!妈住院的钱是我出的!这屋里哪样东西,跟你那点退休金有关系?”
他愣了一下,大概没想到我会顶嘴。平时我忍惯了。他随即更凶:“反了你了!没我儿子,你算个什么东西?滚!”
“杨健是我丈夫,不是我的天。”我往里走了一步,那股甜腥味更重了,“今天这事不说清楚,没完。”
我看清了。绒布上,是几个玻璃罐子,像泡药酒的那种。罐子里液体浑浊,黄黄的。泡着的东西,黑乎乎一团,带着点惨白。
我眯起眼。
是猫。小的,大的,都有。姿态扭曲。
最边上那个小罐子,里面是一只奶猫,眼睛还没睁开的样子,蜷着。
我腿有点软,扶住门框。不是怕,是恶心,一股火从脚底板烧上来。
“你弄的?”我转头看他,声音平了。
公公脸上闪过慌乱,马上又挺起腰杆:“我弄的怎么了?几只畜生,街上捡的,死了也是死了,我废物利用。你管得着吗?”
“废物利用?”我重复一遍,点点头,“妈知道吗?杨健知道吗?”
“你敢!”他猛地跨过来,挡住我跟那些罐子之间,“敢跟他们胡说八道,我让你在这个家待不下去!”
“妈为什么住院?”我没理他的威胁,盯着他,“哮喘突然加重。医生问她接触什么了,她说不出。家里,就你这书房,她定期进来打扫。是你求她打扫的,说里面是你‘重要的收藏’,别人动不得,只有妈能动。是吧?”
他眼神躲闪:“你……你胡扯什么!那是她老毛病!”
“老毛病?”我拿出手机,对着那些罐子,“这味儿,这腐烂的东西泡出来的气味,还有甲醛?防腐剂?正常人闻久了都受不了,妈有哮喘!你是她丈夫!”
“拍什么拍!删了!”他扑过来抢手机。
我退到走廊,背贴着冰冷的墙。“你怕什么?你不是说,几只畜生吗?”
“贱人!把手机给我!”他呼哧喘气,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。
“给你?然后让你砸了?”我把手机塞进内衣里,挑衅地看着他,“来拿啊。”
他僵住了,手指着我抖,骂不出整句。
婆婆就是这时候被吵醒的。她扶着墙,从卧室挪出来,脸色苍白,气短:“吵……吵什么呀……咳咳……”
公公立刻变脸,堆上笑过去扶她:“没事没事,这不懂事的,非要进我书房看看,我说里面乱,她还不高兴了。走走,回去躺着。”
婆婆疑惑地看着我,又看看书房黑洞洞的门。门被我刚才退出来时带上了,但那股味儿,丝丝缕缕飘在空气里。
“小娟,”婆婆轻声问,“你爸书房里……是什么味儿啊?怪怪的。我每次打扫完,都难受好几天。”
“妈!”公公打断她,声音很急,“能有什么味儿!旧书旧报纸的霉味!就你身子金贵!回去躺着!”
我看着婆婆虚弱的样子,她眼里有害怕,不是对气味,是对公公。她一直怕他。
“妈,”我开口,声音稳得我自己都意外,“您先回屋。我和爸,有点事要掰扯清楚。为了您好。”
公公恶狠狠瞪我,那眼神,像要活吃了我。
婆婆看看我,又看看他,最终低下头,默默转身回屋了。关门声很轻。
走廊里只剩我们俩。安静得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。
“你想怎么样?”他压着嗓子,像毒蛇吐信子,“开个价。要钱?我给你。别在杨健和你妈面前乱嚼舌根。”
“钱?”我笑了,“你的钱,不都是妈和杨健给的?我要我自己的钱?”
“那你想怎么样!”他低吼。
“那些东西,”我指指书房,“处理掉。今天。现在。”
“不可能!”他断然拒绝,“那是我的东西!我花了心血!”
“你的心血,就是弄死猫,泡在罐子里?”我逼近一步,“你心理变态啊?”
“你懂个屁!”他被激怒了,口不择言,“那是艺术!生命凝固的艺术!它们死了,我让它们永恒!你这种俗人,根本不明白!”
艺术?我看着他因激动而扭曲的脸,那张平时对婆婆呼来喝去、对我颐指气使的脸。一股寒意爬上脊背。
“我是不明白。”我说,“我也不想明白。我就问你,处理,还是不处理?”
“不处理!”他梗着脖子,“有本事你告诉杨健去!看他信谁!看他向着自己老子,还是向着你这个外人!”
又是这句话。外人。结婚三年,这句话我听了无数次。从他和婆婆嘴里。
“行。”我点点头,不再看他,转身往自己卧室走。
“你去哪?”他在后面喊。
“报警。”我说。
两个字,炸得他魂飞魄散。他冲过来拉住我胳膊:“你疯了!报什么警!这犯法吗?”
“虐待动物,可能不犯死罪。”我甩开他,“但传播血腥恐怖图片视频,扰乱社会治安,够警察上门了吧?还有,妈住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,是不是涉及危害他人健康,让警察和医生来判断。”
我看着他血色一点点从脸上褪去。“你……你敢!”
“你看我敢不敢。”我拿出手机,解锁,当着他面按了“1”。
他彻底慌了,扑通一下,竟然跪了下来,抱住我的腿:“小娟!小娟我错了!你别!别报警!我处理!我马上处理!”
我愣住了。没想到他能跪。这个在家里称王称霸的老头。
“起来。”我声音发冷。
“你答应我,不报警,不告诉杨健和你妈。”他抬头,老泪纵横,不知道是真是假。
“你先处理。”我不松口。
“好,好,我处理。”他爬起来,踉踉跄跄去开书房门。我跟进去。
他颤抖着手,去抱那些罐子。大的罐子很沉,他抱了一下没抱动。
“找个大袋子,装起来,密封好。”我指挥他,像指挥一个犯人,“我跟你一起下楼,扔到小区外面垃圾站。”
他照做了,翻出几个黑色大垃圾袋,把那些“艺术品”一个个装进去,裹了好几层。动作慢,手一直抖。那股甜腥味被裹住,淡了些,但还在。
我们一人提着两个沉重的袋子,下楼。没人说话。夜风一吹,我打了个寒颤。
扔进垃圾站那个绿色大箱子的瞬间,他肩膀塌了下去,像被抽了骨头。
往回走的路上,他在我身后一步远,声音嘶哑:“小娟,这事……就算了吧?爸以后……再也不弄了。”
我没回头。“书房,彻底通风打扫。所有角落,消毒。妈身体好之前,你不准再进去鼓捣任何东西。”
“好,好。”他连声答应。
进了家门,婆婆卧室门关着。我们各自回屋。
我反锁了房门,背靠着门板,滑坐在地上。手还在抖。不是后怕,是愤怒的余震。
手机亮了,是杨健的微信,说他加班,晚点回。我回了个“好”,没多说。
那一晚,我没睡。听着外面动静。公公屋里一直没声音。
接下来几天,风平浪静。公公果然老实了,书房门开着散味,他进去打扫了几次,买了空气清新剂,味道淡了很多。对婆婆,居然有了点笑脸,偶尔还问句“舒服点没”。婆婆受宠若惊,私下跟我说:“你爸是不是老了,转性了?”
我只是说:“可能吧。”
杨健忙他的项目,早出晚归,对这个家的微妙变化毫无察觉。我也没提。不是时候。
但我心里那根刺,没拔掉。那些扭曲的猫的影像,刻在我脑子里。还有他下跪时,眼里一闪而过的,不是悔恨,是狠毒。我看见了。
一个星期后,婆婆出院回家,精神好了很多。家里似乎恢复了平静,甚至比以往“和谐”。
直到那天下午。
我提前下班,想熬点汤。进门,家里静悄悄。婆婆说去楼下晒太阳了。
我放下东西,习惯性扫视客厅。目光落在公公常坐的摇椅旁,垃圾桶里。
有一小团带血的纸巾。还有几根,很细小的,白色的……绒毛。
猫毛?
我心跳漏了一拍。轻手轻脚走过去,用指尖捏起一点绒毛。很软,很细,是奶猫的毛。
血还没完全干透。
他还在弄。
而且,升级了。弄刚出生的奶猫。
我站在原地,血往头上涌。恶心得想吐。上次是死猫,这次,他可能直接……
我不敢想。
书房门关着。我走过去,拧了拧,锁了。钥匙他肯定藏得更严了。
我回到自己房间,关上门,深呼吸。不能硬来。上次是撞见了,逼他处理了“证据”。这次,他肯定更警惕。
我需要证据。确凿的,他无法抵赖的证据。
我在网上搜,买了一个很小的,带录音功能的摄像头。伪装成充电头的样子。第二天就到货了。
趁他下午雷打不动出门遛弯(不知道是真遛弯还是去“找材料”),婆婆在厨房忙活,我溜进书房。快速找了个靠墙插排,把“充电头”插上去,角度正好对着书房中间空地。手机连上,测试了一下,画面声音都很清晰。
做完这些,我手心全是汗。
接下来是等待。我知道,他忍不住。那种“瘾”,戒不掉。
第三天晚上,机会来了。杨健公司团建,不回来。婆婆睡得早。
我早早回房,关灯,假装睡了。手机屏幕亮着,显示书房的监控画面。
十一点多,书房门轻轻响了。他闪身进来,反锁了门。
他手里拎着个小小的,打着结的黑色塑料袋。动作熟练地走到书桌前,打开台灯(光线很暗),从抽屉里拿出新的玻璃罐,还有一瓶不知道什么液体。
然后,他解开了那个黑色塑料袋。
我捂住了嘴。
是一只很小很小的狸花猫,可能就刚满月。一动不动,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他戴上了橡胶手套,拿起一把小剪刀,脸上是一种……专注到虔诚的变态表情。他轻轻抚摸那只小猫,嘴里喃喃自语:“别怕……很快的……你会变成最美的样子……永恒……”
他拿起剪刀,对准了小猫咪的脖子。
我再也看不下去了。手指颤抖着,按下了录像保存,然后直接拨通了110。
“喂,110吗?我要报警。地址是XX小区X栋X单元XXX室。有人正在室内虐杀动物,可能有传播暴力血腥行为的倾向。请你们马上过来。我有现场视频证据。”
我的声音压得很低,但很清晰。
挂掉电话,我听着监控里传来的,他哼着不成调小曲的声音,还有细微的剪子摩擦声。我全身发冷,但脑子异常清醒。
我打开卧室门,走到客厅,打开了所有大灯。然后,我去敲婆婆的门。
“妈,妈你醒醒。出事了。”
婆婆惊醒,披着衣服出来:“怎么了小娟?”
“爸可能在书房里,做不好的事。”我拉着她,走到书房门口,“我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声音。”
婆婆脸色变了,去敲门:“老头子?老头子你在里面干嘛?开门!”
里面的动静戛然而止。一阵慌乱的窸窣声。
“没事!我找东西!睡你的去!”公公的声音隔着门传来,强作镇定。
“你开门!”婆婆提高了声音。
就在这时,楼下传来了警笛声。由远及近,停在了我们这栋楼下。
公公显然也听到了。书房里传来“哐当”一声,像什么东西打翻了。
“谁……谁报警了?”他声音都变了调。
我没说话。婆婆惊恐地看着我。
敲门声响起,是入户门。警察来了。
我去开门。两名警察站在门口,亮了下证件:“我们接到报警,这里有人涉嫌虐待动物?”
“在书房。”我侧身让他们进来,指向紧闭的书房门,“反锁了。我有监控视频,可以给你们看。”
警察点头,一名去敲书房门:“里面的人,开门!警察!”
里面死寂。
警察加重了力道:“开门!否则我们强制破门了!”
过了十几秒,门锁“咔哒”一声开了。公公站在门口,脸白得像纸,手上还戴着沾了血迹的橡胶手套。他身后,书桌上,狼藉一片。小玻璃罐,打翻的液体,黑色塑料袋,还有那把剪刀,和小猫小小的尸体。
一切,无可辩驳。
婆婆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捂住胸口,摇摇欲坠。我扶住她。
警察迅速进去,控制了现场,给公公戴上了手铐。他全程低着头,没看我们任何人。
一名警察查看了我提供的监控录像片段,脸色凝重。“人我们先带走。需要你们,特别是报警人,明天来派出所做详细笔录。这些证据很重要。”
他们带走了公公,也带走了那些“工具”和小猫的尸体。
门关上,家里死一样的静。
婆婆瘫坐在沙发上,无声地流泪,浑身发抖。她终于明白了,她闻到的“怪味”,她莫名的哮喘加重,都源于什么。
我给她倒了杯热水,坐在她旁边。
“小娟……”婆婆抓住我的手,冰凉,“你……你早就知道了?”
“上次妈住院,我发现了。”我低声说,“逼他扔了。我以为他改了。没想到……”
“这个老畜生……这个老畜生啊!”婆婆终于哭出声,是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恶心,“他怎么会变成这样……他以前不这样的啊……”
我搂住她的肩膀,没说话。有些人骨子里的坏,是慢慢露出来的,还是早就藏着,谁说得清呢?
杨健是凌晨回来的,被我叫回来的。他听完,整个人都懵了。看着母亲哭肿的眼,看着我手机里那段不忍直视的监控片段,他抱着头,蹲在地上,半天没起来。
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?”他红着眼睛问我。
“第一次发现,我逼他扔了。我以为能吓住他。”我实话实说,“告诉你,以你的脾气,要么跟他大吵,要么觉得我小题大做。家里更不得安宁。妈还在病着。”
他沉默了。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。他对他爸,一直有种愚孝和逃避。
“这次,我不能忍了。”我说,“这不是癖好,是犯罪。对妈的健康是威胁,对邻居,对社会也是潜在威胁。谁知道他下次会做什么?”
杨健抹了把脸,站起来:“我去派出所。”
公公被拘留了。虐待动物,制作、传播血腥暴力内容,证据确凿。再加上婆婆的医疗记录可以作为间接证据,证明其行为对家人健康造成危害。虽然不会判多重,但足够他留下案底,在小区里,在亲戚朋友面前,彻底“社会性死亡”。
婆婆坚决要求和他离婚。杨健这次没再犹豫,支持母亲。房子是杨健和我的名字,公公没份。他被放出来后,没脸回来,也没地方去,听说租了个远郊的破房子自己住。没人去看他。
家里彻底清净了。那股甜腥味,永远消失了。
婆婆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。她有时会看着我,欲言又止。
终于有一天,她说:“小娟,这个家,多亏了你。妈以前……有些地方,对不住你。”
我摇摇头:“都过去了,妈。”
书房彻底改造了,成了婆婆的阳光花房。里面种满了绿植,生机勃勃。
我再也没见过公公。偶尔听楼下大妈闲聊,说那个租在郊区的怪老头,越来越孤僻,捡垃圾堆里的死老鼠回家,被房东发现,赶走了。后来,就没了音讯。
恶有恶报,不是老天给的,是人自己作的。当你凝视深渊,深渊也在凝视你。他最终,活成了自己“作品”里,那种腐烂的、见不得光的样子。
我和杨健,还是那样。有些裂痕,发生了就是发生了。但日子,总得往前过。
只是我偶尔深夜醒来,还是会想起那些罐子,想起监控画面里他虔诚又残忍的眼神。然后我会起身,去看看婆婆房间门缝下透出的安稳的灯光,或者摸摸身边熟睡的杨健。
这个家,现在干净了。
是我亲手打扫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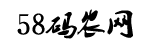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