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# 夜读丨离开手机我们还能“存在”吗
夜晚,放下手机,却仿佛失去了与世界的连接。我们不禁自问:离开手机,我们还能“存在”吗?
"手机的依赖,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。" 它不仅是通讯工具,更是信息获取、娱乐、社交的平台。我们通过手机了解时事,消磨时光,维系与亲友的关系。手机,仿佛成为了我们数字身份的延伸,离开了它,我们仿佛失去了与这个世界的连接。
"这种依赖,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。" 我们是否过度依赖手机,以至于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?我们是否在虚拟世界中迷失了自我,忘记了真实的情感和体验?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,将生活完全掌控在了手机的手中?
"离开手机,我们或许会感到焦虑和不安。" 习惯了即时通讯和信息轰炸,我们可能会难以忍受信息的真空和时间的停滞。习惯了通过手机与世界互动,我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迷茫。
"然而,离开手机,我们也能重新找回自我。" 我们可以拥有更专注的注意力,更深入的思考,更丰富的体验。我们可以更珍惜与亲友的相处时光,更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我们可以更关注现实世界,更探索未知的领域。
"离开手机,我们并非失去了“存在”,而是重新获得了“存在”的意义。" 我们可以摆脱数字世界的束缚,回归真实的生活,感受生命的温度和力量。
"夜深人静,放下手机,让我们思考:
相关内容:
一直都有较为严重的电量焦虑和死机焦虑。我本来以为,这种焦虑是源于与外界失去连接的恐慌,直到某个周六的傍晚,我才发现,有比跟外界失去连接更值得恐慌的东西。
那天我刚和朋友见完面,婉拒了他们的晚餐,从咖啡馆走回家。刚进家门,拿起手机要看时间,发现手机死机了。我把手机插上电源,开始在电脑上搜索手机死机的各种解决办法,从百度到谷歌,试遍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组合键重启方式,手机依然倔强地黑着屏幕。我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顶峰。
但是,抛物线规律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适用的。“还好电脑还在正常工作”,我心想,而且今天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人联系。于是,我从焦虑变得认命,甚至感觉到了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轻松。我试图理解这种不合时宜的轻松感,好像是手机毫无征兆的死机,让我理所应当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任何社交干扰的空间里,可以安静地专心地做一些事情,不需要再被手机控制。
“社交过载”,我脑子里出现这么一个短语,用以总结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在人群中的生活状态。不管主动还是被动、线上还是线下,我好像处于这种状态很久了。
客观来看,高频度社交确实让我们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关系,我们是互相信任的好朋友,是合作很久的工作伙伴,是伴侣。哪怕现实中不会每天见面,但线上仍能时刻保持联系。然而,时不时地,在推杯换盏间、在看着对面的人不断述说着什么时,内心会升起疑惑,我是谁?他是谁?他们是谁?在手机死机、被动抽离社交活动的现在,我终于有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,为什么会偶尔觉得跟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亲近感和亲密感,以及由此产生对所谓的“社交”的质疑。
不得不承认似乎真实存在的两种情况。一种是,我自己好像对别人并没有发自内心的亲近和关心,这也应该导致了另一种完全不客观的情况——我觉得别人对我的关心、友善、帮助等等行为,也是出于角色和礼貌。
这难道也是一种“现代病”吗?是一种“大都市病”吗?抑或是,从古至今在人类社群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?想到这里,我突然理解了索尔斯塔《第11部小说,第18本书》里主人公最后那荒诞的行为。
当意识到这种莫名的或者说原始存在的虚无感时,我们必然会本能地感到不适,于是有了质疑,有了思考,然后试图采取一些行动来反抗这种虚无感。这些行动可能是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交关系、重新审视自己,也可能是更激进的、更戏剧性的,比如主动切断一些联系,比如像索尔斯塔的小说里主人公把自己变成残疾人。但是之后呢?我们是否可以在切断联系这个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什么真谛?这种激烈的扭转社交虚无的荒诞行为是否真的如想象般有效?在自己人为制造的社交真空或其他荒诞的状态中,我们是否真的会感觉更加接近真实、更加舒适?
不难预测的是,无论是哪种方式和哪种意义的“切断”,可能都难以持续。有两方面的原因大概可以解释这种必然的失败:第一,熟悉的日常生活状态的惯性实在太大;第二,为了解决社交的虚无从而选择进入只有自己存在的状态里,但随即便被完全面对自我时那种更深的虚无吓退,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人群。
傍晚,窗外层楼之后的夕阳已落下大半,呈现出鲜亮的橘色,周围的云也被一层一层地染成橘色、浓粉色、浅粉色,再是调色盘很难调出的粉蓝色。我看着黑着屏幕的手机感到一丝惋惜,想着如果手机没有死机的话,就可以把这漂亮的落日晚霞拍下来了,发到群里、发到朋友圈、发到微博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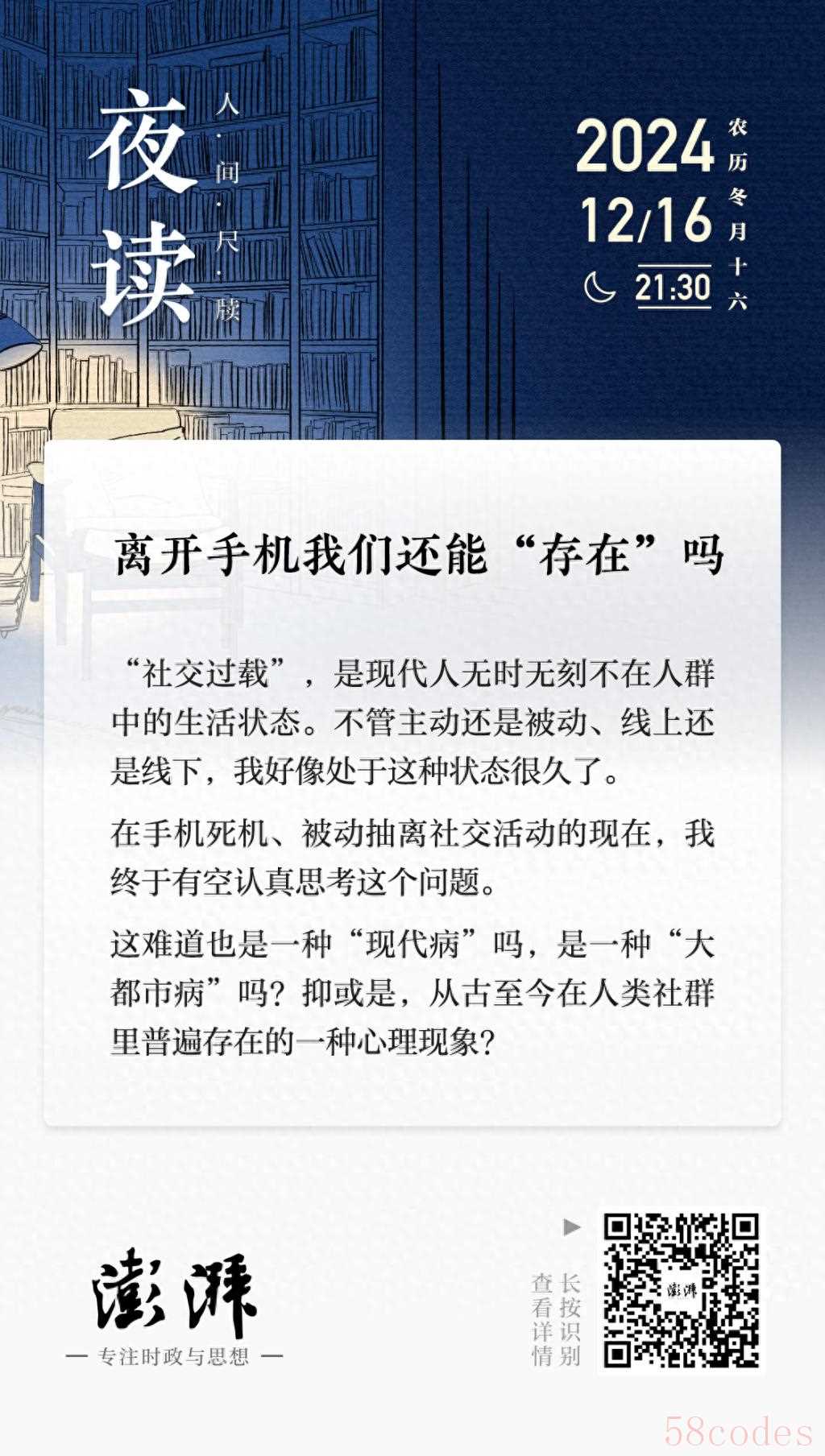
程维维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