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反转的故事开头。我们来续写一下:
---
"故事续写:"
“我给你婚礼,只跟夏晴领证。” 我的声音透过电话,异常清晰,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电话那头,是我在商场上雷厉风行多年的合伙人,也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,江皓。我们之间的联姻,是家族利益的结合,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,只剩下走形式的那一步。
我挂了电话,脸上没有丝毫波澜。江皓是江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,家世显赫,能力出众,是许多人眼中理想的对象。而我,林氏集团的新任CEO,同样身经百战。我们之间的结合,从世俗角度看是天作之合。但我心里清楚,这不过是各取所需的游戏,感情?那太奢侈。
我的目标,或者说,我内心深处那个连自己都未必完全承认的渴望,是夏晴。那个阳光开朗,笑起来眼睛像星星的女孩。我们相识于一场商业论坛,她纯粹、善良,与我周旋于名利场的世界截然不同。和她在一起的时候,我仿佛看到了久违的平静和真实。我知道,我们的身份差距巨大,我们的未来也注定不可能,但我还是无法控制地被她吸引。
所以,我决定,要为自己争取一次。用一场盛大却只有我和夏晴知道的婚礼,来对抗那场早已注定的、充满利益交换的
相关内容:
雨下得很大。
像要把整座城市都洗刷一遍。
我站在高铁站的出站口,看着玻璃幕墙外被灯光切割成千万条亮线的雨水,觉得有些冷。
沈舟的消息是三分钟前发来的。
“晴晴,车晚点了,还要半小时。”
我回了一个“好”,然后收起手机,把手插进大衣口袋。
口袋里,我的指尖触碰到的,是另一部手机的冰冷边缘。
是沈舟的备用机。
他出差前落在家里的。
两天前,我无意间点亮了它。
屏幕上弹出的那条推送信息,来自一个出行APP。
“您关注的常用同行人‘小安’已出发,G1375次列车预计20:45抵达南站。”
小安。
不是“安然”。
也不是任何一个我认识的,带着“安”字的朋友。
只是一个亲昵的,不带姓氏的,藏在常用同行人列表里的“小安”。
我跟沈舟结婚七年。
我们是大学同学,毕业就结了婚,从一无所有到在这座城市扎下根。
他做建筑设计,我做企业法务。
我们是外人眼里最标准、最契合的伴侣。
唯一的遗憾,是我们没有孩子。
去医院检查过很多次,双方都没问题,医生说,是概率。
概率。
多么冰冷又精准的词。
就像此刻我攥在口袋里的这部手机,它用一个同样精准的算法,推送了一条我本不该看到的信息。
我抬起头,看着出站口上方巨大的电子屏。
G1375,来自他出差的城市,正在进站。
人群开始涌动。
我没有动。
我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,像一尊淋了雨的石像。
看着他和一个年轻女孩并肩走出来。
女孩很年轻,二十出头的样子,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长款羽绒服,衬得一张脸小而白净。
她仰着头在跟沈舟说话,眼睛里有光。
那种光,我曾经也有过。
沈舟在笑,侧脸的线条柔和。他手里推着两个行李箱,一个是他的,另一个是粉色的。
他看见了我。
脸上的笑容,像被瞬间按下了暂停键。
他身边的女孩也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来,表情有些茫然,然后是局促。
我看着他们,没有走过去。
风从开启的门里灌进来,吹起我的头发。
我只是平静地,甚至带着一丝礼貌的审视,看着我的丈夫,和他身边的“小安”。
沈舟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他松开推着行李箱的手,朝我走过来。
“晴晴,你怎么来了?不是说雨大,让你别出门吗?”
他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我能轻易分辨出的慌乱。
我没有他的问题。
我的目光越过他,落在他身后那个女孩身上。
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,抓紧了自己的背包带。
“不介绍一下吗?”我开口,声音平稳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。
沈舟的身体僵硬了。
雨声,广播声,人群的嘈杂声,在这一刻仿佛都变成了遥远的背景音。
世界在我、沈舟,和那个叫“小安”的女孩之间,拉开了一道无形的屏障。
“这是安然,”沈舟的声音有些干涩,“公司的实习生,这次跟我一起出差。”
安然。
原来她叫安然。
我点了点头,像是接受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介绍。
然后,我从口袋里拿出那部备用机,递到沈舟面前。
“你的手机。”
屏幕还亮着,那条推送信息清晰可见。
沈舟的脸色,一瞬间变得惨白。
他没有接。
我把手机塞进他大衣的口袋里,动作轻柔,像是在为他整理衣领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,“回家。”
两天前。
那是一个寻常的周六清晨。
我被阳光叫醒,沈舟已经不在身边。
他要去邻市参加一个行业峰会,周一晚上回来。
我起床,给他收拾行李箱。
衬衫,西裤,剃须刀,还有他常用的胃药。
一切都井井有条。
他的备用机就放在床头柜上充电,是他前一天晚上换下来的。
他说新手机的电池更耐用。
我拔下充电线,准备把它放进抽屉。
就在那时,屏幕亮了。
“您关注的常用同行人‘小安’已出发……”
我的动作停住了。
常用同行人。
这个功能我没用过,但顾名思义,不难理解。
我盯着那个陌生的昵称,“小安”。
心里某个地方,像被针尖轻轻刺了一下。
不疼,但是很清晰。
我没有立刻去质问,也没有歇斯底里。
我只是把那部手机放进了我的包里。
然后,像往常一样,给他发了条微信。
“东西都收拾好了,路上小心。”
他很快回复:“好,老婆辛苦了。”
后面跟了一个拥抱的表情。
那两天,我照常上班,下班,健身,看书。
生活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,没有因为那个小小的发现而出现任何故障。
我甚至抽空回了一趟家,见了我的父母。
我父亲是做实业的,家族企业不大不小,但在本地颇有声望。
当初我执意要嫁给一穷二白的沈舟,留在另一个城市,家里是极力反对的。
是我母亲,顶着压力,说服了我父亲。
“女儿喜欢,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母亲给我炖了汤,拉着我的手,又说起孩子的事。
“晴晴啊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你和阿舟都还年轻。”
我笑着点头,喝着那碗温热的汤。
汤很好喝,暖意从胃里一直蔓延到四肢。
但心里那个被针刺过的地方,却始终是凉的。
临走时,父亲把我叫到书房。
他没提沈舟,也没提孩子。
他只说:“晴晴,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。任何时候,受了委屈,就回来。”
我看着父亲鬓边新增的白发,点了点头。
“爸,我知道。”
从家里出来,我开车去了公司。
我用我的权限,调取了公司法务部合作的一家调查机构的联系方式。
我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。
邮件内容很简单。
“帮我查一个人,安然。以及她和沈舟的所有同行记录。”
附件里,是沈舟的身份证号,和那个出行APP的截图。
我不是一个喜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人。
我喜欢证据。
喜欢在一切摊牌之前,手里握有绝对的筹码。
就像在法庭上,情感永远是最无力的辩护。
事实和证据才是。
回家的路上,车里死一样的寂静。
沈舟开车,安然坐在后座。
我坐在副驾。
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规律地摆动,发出单调的“唰唰”声。
我能从后视镜里,看到那个女孩苍白的脸。
她一直低着头,手指绞着衣角。
沈舟几次想开口,都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我平静的眼神,然后把话咽了回去。
他怕的,不是我哭,不是我闹。
他怕的是我现在的样子。
太冷静了。
冷静得像一个局外人,一个法官。
而不是他的妻子。
车开到我们住的小区楼下。
我解开安全带。
“你先送她回去吧。”我说。
沈舟愣住了,“晴晴……”
“送她回去。”我重复了一遍,语气不容置喙,“这么晚了,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”
我推开车门,下了车。
雨丝斜斜地飘过来,打在我的脸上,冰凉。
我没有回头,径直走进单元门。
我没有带伞。
我就是要让他看着我的背影,被这冰冷的雨水一点点浸湿。
我要让他知道,有些东西,一旦湿了,就再也暖不回来了。
回到家,我脱掉湿漉漉的大衣,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。
出来的时候,沈舟已经回来了。
他站在客厅中央,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手足无措。
茶几上,放着他给我带的礼物。
一条丝巾,我喜欢的牌子,最新款的颜色。
往常,我会很开心地收下,抱着他亲一下。
今天,我只是瞥了一眼,就移开了目光。
“坐吧。”我说。
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,擦着湿漉漉的头发。
“晴晴,我……”
“我先说。”我打断他。
我把毛巾放到一边,身体微微前倾,看着他的眼睛。
“第一,她是谁?”
“安然,公司的实习生。”他的声音很低。
“第二,多久了?”
他沉默了。
嘴唇紧紧抿着,下颌线绷得很紧。
“半年。”最终,他还是说了出来。
半年。
三百六十个日夜,我们共享一张床,他心里却装着另一个人。
我的心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,疼得有些呼吸不畅。
但我脸上,依旧没什么表情。
“第三,到哪一步了?”
这个问题,像一把锋利的刀,直直插进我们之间。
沈舟的眼睛红了。
他抬起头,看着我,眼神里是痛苦,是挣扎,是哀求。
“晴晴,对不起。”
他说,“是我混蛋。”
我没说话。
我在等一个明确的答案,而不是一句廉价的道歉。
他似乎明白了。
他闭上眼,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“……所有。”
这两个字,很轻。
却像两颗子弹,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心脏。
原来,婚姻这间我以为固若金汤的房子,早就被白蚁蛀空了。
我只是那个最后知道的,愚蠢的房主。
我靠在沙发上,忽然觉得很累。
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。
“沈舟。”我叫他的名字。
“嗯。”
“我们谈谈吧。”我说,“不是作为夫妻,是作为两个成年人,两个合同的签署方。”
他猛地抬起头,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
“我们的婚姻,本质上是一份契约。”我继续说,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份法律文件。
“契约里,有权利,也有义务。”
“共同财产的支配权,是权利。彼此忠诚,是义务。”
“现在,你违约了。”
第二天,我约了安然。
就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馆。
我到的时候,她已经在了。
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毛衣,素面朝天,看起来比昨天更小了。
见到我,她紧张地站了起来,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“夏……夏姐。”
“坐吧。”我指了指对面的位置。
我给她点了一杯热牛奶。
“别紧张。”我说,“我今天找你,不是来指责你,也不是来伤害你。”
她捧着牛奶杯,低着头,小声说:“对不起。”
“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”我看着她,“你应该道歉的对象,是你自己的人生。”
她愣住了,抬起头看我。
“沈舟跟你说什么了?”我问。
“他说……他说你们感情不好,早就想离婚了。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,“他说他喜欢我,喜欢跟我在一起时,那种轻松的感觉。”
我笑了。
多么标准,多么经典的台词。
每一个出轨的男人,都会对第三者这样说。
把自己的妻子,描绘成一个面目可憎,毫无生趣的怨妇。
把自己的背叛,美化成追求真爱,挣脱牢笼的壮举。
“他跟你说,我们没有孩子,对吗?”
她点了点头。
“他说,是因为我生不出来,所以我们之间早就没有爱了,只剩下责任。”
我端起面前的咖啡,喝了一口。
很苦。
“安然,你今年多大?”
“二十三。”
“大学刚毕业?”
“嗯,去年毕业的。”
“很好的年纪。”我说,“明亮,干净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”
“沈舟比你大十岁。他有事业,有阅历,看起来成熟稳重,能给你安全感,对吗?”
她咬着嘴唇,没说话,但眼神已经给了我答案。
“他给你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会离婚,然后娶你,给你一个家,一个婚礼,一个孩子。”
“你信了。”
我不是在问她,我是在陈述。
安然的眼泪,一滴一滴,掉进了牛奶杯里。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们……”
“你当然知道。”我打断她,“你只是选择性地忽略了我的存在。或者说,你相信了他口中那个‘我’的版本。”
“安D然,我今天来,不是来跟你抢男人的。”
我的语气很平静,甚至有些温和。
“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些事实。”
“第一,我和沈舟的感情,在昨天之前,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至少在我看来。”
“第二,关于孩子,不是我生不出来。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,在事业稳定前,暂时不要。”
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沈舟,他不会离婚。”
安然猛地抬起头,泪眼婆娑地看着我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他不敢。”我说,“我和他,不仅仅是夫妻。我们的财产,我们的人脉,我们的社会关系,早就深度绑定了。”
“更何况,他现在这个设计院副院长的位置,有我父亲一半的功劳。”
“离婚,他会净身出户,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。你觉得,他会为了你口中的‘爱情’,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?”
安然的脸,一寸一寸地白了下去。
她眼里的光,也一点一点地熄灭了。
我看着她,忽然觉得有些可悲。
为她,也为我自己。
我们都爱上了一个,精心为我们编织谎言的男人。
“我不是来劝你离开他的。”我最后说。
“我甚至,可以成全你们。”
安然的眼睛里,露出一丝困惑和不解。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就是,”我看着她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可以给他一场婚礼,一场盛大的,所有人都知道的婚礼。”
“新娘,是你。”
和安然谈完,我直接回了家。
沈舟请了假,在家里等我。
他一夜没睡,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,整个人看起来颓废又憔悴。
看到我回来,他立刻站了起来。
“晴晴,你去找她了?”
“嗯。”
“你别为难她,所有事都是我的错。”他急切地说。
“我没有为难她。”我把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,“我只是去跟她,达成了一个共识。”
我走到他面前。
“沈舟,你想给她一个未来,对吗?”
他愣住了。
“你想给她名分,想让她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躲躲藏藏。”
“你想娶她。”
我的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锤子,敲在他的心上。
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“晴"晴,我们……”
“你不用解释。”我说,“我理解。”
“安然年轻,漂亮,单纯。她崇拜你,依赖你。跟你在一起,你能找回久违的,被需要的感觉。”
“而我,太独立,太冷静,太像你的战友,而不是你的妻子。”
“尤其是在孩子这件事上,我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,表现出强烈的渴望。这让你觉得,我们的家,缺了点什么。”
“所以,你需要在外面,找一个能给你温暖,能让你感觉到自己还是个‘男人’的人。”
“我说得对吗?”
沈舟看着我,嘴唇颤抖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我的平静和理智,是他最害怕的武器。
它剥开了他所有自欺欺人的借口,把他内心最深处的懦弱和自私,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“我不会跟你离婚。”我说。
他猛地抬起头。
“但是,我可以给你一场婚礼。”
他眼里的震惊,几乎要溢出来。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?”
“我说,我可以让你和安然,办一场婚礼。”
我从包里,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。
一份协议。
我亲手草拟的。
“这是我们的‘新婚姻协议’,或者说,是我们这段破裂关系的‘风险管控方案’。”
我把协议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。
“第一,我们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保持不变。你我,依然是合法夫妻。”
“第二,所有婚内共同财产,包括房产,车辆,存款,股权,全部转移到我个人名下。我会给你一部分现金,作为你未来三年的生活开支。”
“第三,你可以和安然举办婚礼,以你‘沈舟先生’的名义。但是,你们不能领取结婚证。对外,你们是夫妻。但对内,她只是你的同居伴告侣。”
“第四,婚礼的所有开销,由你个人承担。你可以动用我给你的那笔生活费。”
“第五,在我们的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,你和安然所生的任何子女,在法律上,与我无关,也不享有我们婚内财产的任何继承权。当然,作为父亲,你需要承担抚养义务。”
“第六,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这份协议,需要你,我,还有安然,我们三个人共同签字,并且进行公证。”
我一条一条地念着。
我的声音,清晰,冷静,不带一丝感情。
像一个冰冷的机器。
沈舟的脸色,从震惊,到不解,再到恐惧。
他看着我,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“晴晴…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他的声音在发抖,“你这是在羞辱我,也是在羞辱她。”
“羞辱?”我笑了。
“沈舟,这不是羞辱,这是规则。”
“是你,先破坏了我们之间的规则。现在,我只是在重建一个新的规则。”
“一个能保护我,也能满足你的规则。”
“你想想,这个方案,对你,对她,对我,都是最优解。”
“对我来说,我保住了我的婚姻,我的财产,我的社会体面。我不用面对离婚带来的种种麻烦和非议。”
“对你来说,你不用净身出户,不用失去现在的一切。你还能如愿以偿地,给你的小情、人一个‘名分’,一场她梦寐以求的婚礼。你可以在她身上,继续寻找你的‘轻松感’和‘安全感’。”
“对安然来说,她得到了她想要的。一个公开的身份,一场盛大的仪式。她可以告诉所有人,她是沈太太。虽然,只是名义上的。”
我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
“我给了你选择。一个体面的,能让所有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选择。”
“当然,你也可以选择不同意。”
“那么,我们就法庭见。”
“我会提交你出轨的所有证据。通话记录,转账记录,同行记录,还有你那部备用机里的所有东西。”
“我会让你,净身出户。”
“我会让你,身败名裂。”
“沈舟,你知道的,我做得到。”
空气,仿佛凝固了。
客厅里,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沉重的呼吸声。
许久。
他抬起手,拿起了那份协议。
他的手,在抖。
一页,一页,他看得极其缓慢。
最后,他抬起头,眼睛里是彻底的绝望和死寂。
“我签。”
他说。
安然也签了。
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的公证处。
她看起来很憔usch悴,眼睛红肿,像是哭了很久。
签完字,她对我鞠了一躬。
“夏姐,谢谢你。”
我不知道她谢我什么。
谢我没有赶尽杀绝?
还是谢我,给了她一场,看似圆满的幻梦?
我没说话。
我只是觉得,生活真是个巨大的柠檬。
酸涩,苦楚。
有的人选择把它丢掉。
而我,选择把它榨成一杯柠檬水。
虽然味道依然不好,但至少,看起来,像一杯正常的饮料。
从那天起,我们的生活,进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。
沈舟开始忙碌起来。
忙着筹备他和安然的婚礼。
订酒店,选婚纱,拍婚纱照。
他会跟我报备他的行程。
“晴晴,我今天下午要去试礼服。”
“晴晴,婚庆公司把方案发过来了,你……要不要看看?”
我一概:“你决定就好。”
我像一个仁慈的,高高在上的女王。
批准了他所有的请求。
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。
身上,偶尔会带着不属于我的,陌生的香水味。
我们不再同床。
他睡在客房。
我们之间,除了必要的交流,再无其他。
家,变成了一个冰冷的,只提供住宿功能的旅馆。
但奇怪的是,他对我,反而比以前更“好”了。
他会记得给我买我喜欢吃的蛋糕。
会在下雨天,提前打电话提醒我带伞。
会像以前一样,在我加班晚归时,给我留一盏灯,和一碗温热的汤。
有一次,我喝着他炖的汤,问他。
“沈舟,你恨我吗?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摇了摇头。
“不恨。”他说,“是我欠你的。”
“晴...晴,”他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,“我知道,你这么做,不是为了报复。”
“你是想用这种方式,把我们重新绑在一起。”
“你是在……挽回我。”
我放下汤碗,笑了。
“挽回?”
“沈舟,你搞错了。”
“我不是在挽回你。我是在清点我的资产。”
“你,也是我的资产之一。虽然出现了折旧,有了瑕疵。但在找到替代品之前,我需要对它进行维修和管控。”
“克制不是恩赐,是义务。忠诚不是选择,是合同条款。”
“我不是善良,我只是不喜欢我的东西,变得肮脏,失控。”
我说完,站起身,走回我的房间。
留下他一个人,在清冷的灯光下,对着一碗慢慢变凉的汤。
婚礼定在两个月后。
地点在沈舟的老家。
一个不大,但很看重传统的北方城市。
他的父母,早就对我们没孩子这件事,颇有微词。
现在听说他要“再婚”,娶一个年轻漂亮,据说已经“有好消息”的女孩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他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
电话是沈舟的母亲打来的。
语气里,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歉意,和掩饰不住的喜悦。
“晴晴啊,阿舟的事……是我们对不起你。”
“但是你也知道,我们沈家,就他这么一根独苗。我们……我们想抱孙子。”
“你放心,离婚了,我们也不会亏待你。房子,车子,都给你。我们再给你一笔钱。”
我静静地听着。
没有解释,也没有反驳。
“阿姨,”我等她说完了,才开口,“您放心,我不会让您和叔叔失望的。阿舟的婚礼,一定会办得风风光光。”
挂了电话,我看着窗外。
树叶已经开始变黄。
秋天要来了。
沈舟那边,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他把安然送回了老家,让她安心待嫁。
他自己,则在公司和老家之间两头跑。
他瘦了很多,也沉默了很多。
有时候我半夜醒来,会看到客房的门缝里,透出微弱的灯光。
我知道,他也没睡。
我们像两个被困在同一座孤岛上的囚徒。
白天,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
夜晚,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。
婚礼前一周,沈舟回家来取东西。
他收拾了一个行李箱,都是一些在老家要穿的礼服和日常衣物。
临走前,他站在门口,看着我。
“晴晴,你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“什么?”
“你会来吗?”
“去哪?”
“我的婚礼。”
我看着他,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
“沈舟,你觉得,我应该去吗?”
他低下头,像是说错话的孩子。
“对不起。”
“没什么对不起的。”我说,“好好办。别搞砸了。”
“毕竟,这不仅仅是你的婚礼。”
“也是我的‘项目’。”
他走了。
家里,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我打开冰箱,里面空空如也。
才发现,已经很久,没有人为我准备食物了。
那碗曾经象征着“家”的汤,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
我关上冰箱门,靠在上面。
巨大的空虚和疲惫,像潮水一样,将我淹没。
我以为我足够强大,足够冷静。
我以为我可以像处理一个棘手的案子一样,处理我破碎的婚姻。
制定规则,签署协议,管控风险。
可我忘了。
人心,不是合同。
感情,不是条款。
那个曾经会在深夜,把我冰冷的脚,放进他怀里焐热的男人。
那个曾经会在我生病时,整夜不睡守着我的男人。
那个曾经会在我受了委"屈时,笨拙地抱着我,说“别怕,有我呢”的男人。
他要去娶别的女人了。
哪怕,那只是一场,由我亲手策划的,虚假的婚礼。
我的眼泪,终于,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
婚礼当天。
天气很好。
我没有去沈舟的老家。
我在我们的家里。
那个红色的结婚证,被我从抽屉的最深处翻了出来。
上面,我和沈舟笑得一脸青涩。
那年,我二十三岁,他也才二十三岁。
我们以为,牵了手,就是一辈子。
手机响了。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我划开接听。
“是夏晴,夏小姐吗?”
电话那头,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,带着浓重的口音。
“我是。”
“我是安然的妈妈。”
我的心,咯噔一下。
“阿姨,您好。”
“夏小姐,我知道,是我们家安然对不起你。”女人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恳求,“但是,孩子是无辜的。”
“她已经,有了三个月的身孕。”
“我知道你和沈舟签了什么协议。安然都跟我说了。”
“她说,你是个好人,是个有大本事的人。”
“所以,我想求求你。”
“求你,高抬贵生手,跟沈舟把婚离了,成全他们吧。”
“我们家不要你们一分钱,只要沈舟这个人,只要我外孙,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”
我握着手机,说不出话来。
安然怀孕了。
这件事,沈舟没有告诉我。
协议里,我们约定了子女的问题。
但我没想到,问题会来得这么快。
“夏小姐,你在听吗?”
“我在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稳。
“阿姨,这件事,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”
“你得去问沈舟。”
“我问过他了!”女人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,“那个没良心的!他说,他这辈子,都不会跟你离婚!”
“他说,他欠你的,要用一辈子来还!”
“夏小姐,你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?”
“我女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等不起了啊!”
我挂了电话。
窗外的阳光,照在我的脸上,却没有一丝暖意。
我看着手里的结婚证。
沈舟说,他不会跟我离婚。
他说,他要用一辈子来还。
这是愧疚?
还是……爱?
我忽然有些分不清了。
我打开电视,调到了本地新闻频道。
婚礼的时间,是中午十二点。
现在是十一点半。
我倒了一杯红酒,坐在沙发上,静静地等着。
等着看,我亲手导演的这场大戏,如何收场。
手机又响了。
这一次,是沈舟的伴郎,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,周宇。
他的声音,听起来无比焦急。
“嫂子!不好了!出事了!”
“沈舟他……他悔婚了!”
我握着酒杯的手,微微一顿。
“怎么回事?”
“他……他在台上,当着所有宾客的面,说……”周宇的声音有些结巴,“他说,他要感谢一个女人。”
“他说,他是个混蛋,他辜负了她七年的感情。”
“他说,这场婚礼,从头到尾,都是一个错误。”
“然后,他把新娘一个人丢在台上,跑了!”
“现在,两家人都快打起来了!乱成一锅粥了!”
“嫂子,你快想想办法啊!沈舟的电话也打不通,他能去哪啊?”
我挂了电话。
房间里,一片寂静。
阳光透过落地窗,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
我看着手中的红酒,殷红的液体,在杯壁上,挂出一道道泪痕。
他悔婚了。
他没有按照我的剧本,演下去。
他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。
这个男人。
这个我以为,已经被我牢牢掌控在手心里的男人。
他用最激烈,最不堪的方式,给了我一个,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局。
门铃,在这时响了。
我没有动。
门铃固执地,一遍又一遍地响着。
最后,变成了用力的敲门声。
“晴晴!开门!我知道你在里面!”
是沈舟的声音。
他的声音里,带着喘息,带着疲惫,还带着一丝……我从未听过的,孤注一掷的决绝。
我走过去,打开了门。
他站在门口。
身上,还穿着那套崭新的,本该属于他和另一个女人的,新郎礼服。
他的头发乱了,领结也歪了。
眼睛里,布满了血丝。
他就那样看着我,一动不动。
我们对视着。
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“婚礼,”我淡淡地开口,打破了沉默,“结束了?”
“结束了。”他哑声说。
“新娘呢?”
“我把她,交给了她的父母。”
“你自己的父母呢?”
“他们……”他苦笑了一下,“大概,已经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”
“所以,”我看着他,“你现在,一无所有了。”
“是。”他点头,“我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“那你来找我做什么?”
“晴晴,”他往前走了一步,几乎要贴到我的身上。
我能闻到他身上,混合着汗水和古龙水的味道。
他伸出手,想要抓住我的胳膊。
我后退了一步,避开了。
他的手,僵在了半空中。
“晴晴,”他看着我,眼睛里,是我从未见过的脆弱和哀求。
“我错了。”
“我知道,现在说这些,已经晚了。”
“我不求你原谅我。”
“我只是想告诉你……”
“从我签下那份协议开始,从我筹备那场荒唐的婚礼开始,我每天,每时,每刻,都在想你。”
“我想起我们大学的时候,我为了给你买一个生日礼物,去工地搬了一个月的砖。”
“我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,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,吃着泡面,也觉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”
“我想起你为了支持我的事业,放弃了家里的安排,陪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打拼。”
“我想起我们说好的,要一起去很多地方旅行,要一起看遍世界的风景。”
“晴晴,那些日子,我没有一天忘记过。”
“是我……是我被名利,被压力,被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,蒙蔽了双眼。”
“我把我们之间最珍贵的东西,弄丢了。”
“那场婚礼,像一面镜子。我看着镜子里,那个穿着礼服,满脸假笑的自己,我觉得恶心。”
“那不是我。”
“我要找回的,不是安然,不是一个新的家庭,不是一个孩子。”
“我要找回的,是你。”
“是那个,会因为我一句话,就笑得像个傻瓜的夏晴。”
“是那个,会陪我熬夜画图,给我递上一杯热牛奶的夏晴。”
“是那个,我沈舟,发誓要爱一辈子的,我的妻子,夏晴。”
他的眼泪,流了下来。
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,在我面前,哭得像个孩子。
我静静地看着他。
心里,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是感动吗?
或许有一点。
但更多的,是荒凉。
有些东西,碎了,就是碎了。
即便用再好的胶水,也粘不回原来的样子。
“说完了吗?”我问。
他愣住了,眼泪还挂在脸上。
“说完了,就回去吧。”我说,“这里,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”
我准备关上门。
他却用身体,死死地抵住了门。
“晴晴!你再给我一次机会!”
“我什么都不要了!工作,房子,钱,我什么都不要了!”
“我只要你!”
“我们重新开始,好不好?”
重新开始?
多么轻飘飘的四个字。
我看着他。
“沈舟,你知道吗?”
“你今天在婚礼上的所作所为,看起来很深情,很勇敢。”
“但实际上,是彻头彻尾的自私和不负责任。”
“你伤害了我,又去伤害安然。”
“你让你的父母,在所有亲朋好友面前,颜面尽失。”
“你毁了所有人的生活,只为了成全你一个人,迟来的,廉价的‘醒悟’。”
“你不是英雄。”
“你只是一个,把所有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,懦夫。”
我的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刀,插进他的胸膛。
他的脸色,变得惨白。
抵着门的手,也渐渐松开了。
我趁机,关上了门。
把他的世界,和我的世界,彻底隔绝。
我靠在门上,听着门外,他逐渐远去的,踉跄的脚步声。
然后,是电梯门打开,又合上的声音。
一切,都安静了。
我缓缓地,滑坐在地上。
眼泪,再一次,无法控制地涌了出来。
我赢了吗?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,这场由我主导的,漫长的战役,终于结束了。
而我,是那个,站在废墟上,唯一的幸存者。
尾声。
我向沈舟的公司,递交了离婚协议和资产分割申请。
一切,都按照我们最初签署的那份协议执行。
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
全程,他都没有再出现。
是他的律师,代他处理了一切。
我重新回到了我父母的城市。
父亲没有多问,只是给了我一个拥抱。
“回来就好。”
我进了父亲的公司,从基层开始做起。
生活,似乎又回到了正轨。
只是偶尔,在深夜,我还是会想起沈舟。
想起他最后站在门口,看着我的那个眼神。
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过得怎么样。
我们,像是两条相交后,又渐行渐远的直线。
再无交集。
直到半年后的一天。
我收到一个快递。
没有寄件人信息。
打开来,里面是一个小小的,用红布包着的玉坠。
是我当年,送给沈舟的护身符。
玉坠下面,压着一张纸条。
纸条上,只有一行字。
字迹,是他的。
“等我。”
我捏着那张纸条,站在窗前,看了很久很久。
窗外,阳光正好。
我的手机,在这时,轻轻震动了一下。
是一条短信。
来自一个陌生的,海外的号码。
短信内容很短。
“夏小姐,我是安然。我现在很好,孩子也很好。但是,关于沈舟,我有一些事情,必须当面告诉你。这关系到你,也关系到他,甚至关系到你父亲的公司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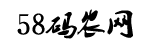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